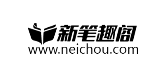第3章:父母
刘承那句“等我下一首”像颗小石子,在周媚鱼心湖里荡开一圈涟漪,还没等涟漪散尽,他人已经转身走了,留下一个清瘦又有点拽的背影。
周媚鱼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心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最终化作一个轻微的蹙眉。这个刘承,和以前那个沉默得近乎透明的男生,判若两人。
而刘承,在转身的刹那,脸上那点刻意维持的平静就有些挂不住了。
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一下,又一下,沉重而急切。
父母。
这个词汇在他舌尖滚过,带着两世为人的重量和酸楚。上一世,他忙于构建他的商业帝国,像个永不停歇的陀螺,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功成名就就是最好的报答。可等他终于停下脚步,回过头,父母早已两鬓斑白,身形佝偻,在他病榻前强忍泪水的模样,成了他上一世最后、也最痛的记忆。
子欲养而亲不待。不,比那更残忍,是亲尚在,他却已无力承欢膝下。
现在,他回来了。回到了他们还未老去,他还未让他们操碎了心的年岁。
放学的铃声像是赦令,他几乎是第一个冲出教室的,书包甩在肩上,脚步快得带风,掠过那些还在为《将进酒》震撼议论的同学,掠过正用复杂眼神看着他的周媚鱼,一心只想快点,再快点,回到那个记忆深处,温暖又有些陈旧的家。
循着模糊又清晰的记忆,他穿过几条熟悉的街道,拐进一个老旧的居民小区。墙壁上爬着些斑驳的苔藓,楼道里弥漫着各家各户晚饭的混合香气。
站在那扇漆色有些剥落的暗红色铁门前,刘承深吸了一口气,才抬手,敲了敲门。
“来了来了!”里面传来一个熟悉到让他眼眶发酸的女声,带着点急促,伴随着拖鞋啪嗒啪嗒走近的声音。
门“吱呀”一声开了。
门后站着的,正是他的母亲,李素珍。
不是病床边那个憔悴哀伤的中年妇人,眼前的母亲,看起来不过四十出头,围着一条有些年头的碎花围裙,上面还沾着点面粉和油渍。她的头发乌黑,在脑后简单地挽了一个髻,几缕碎发垂在耳边,脸上带着常年操劳的细纹,但气色红润,眼神明亮,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她看到刘承,眼里立刻漾开纯粹的笑意,那笑意瞬间抚平了刘承心头翻涌的惊涛骇浪。
“承承回来啦?今天怎么跑得一头汗?快进来快进来,妈正炸你爱吃的椒盐小酥肉呢!”她一边说着,一边自然而然地伸手,想帮刘承把肩上的书包拿下来。
刘承喉头哽了一下,侧身避开:“妈,我自己来。”他的声音有点哑。
他换鞋进屋,目光急切地扫过不大的客厅。
父亲刘建国正坐在旧沙发上,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份今天的晚报。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工装,大概是刚下班不久。父亲的背影依旧宽厚,但坐姿很端正,带着他们那一代人特有的、经过部队锤炼的挺拔。听到动静,他放下报纸,转过头。
父亲的相貌是标准的国字脸,眉毛浓黑,眼神沉稳,额角和嘴角有着深深浅浅的皱纹,那是岁月和辛劳刻下的印记。他看到刘承,脸上没什么太明显的表情,只是点了点头,声音不高,却带着一家之主的沉稳:“回来了?洗手,准备吃饭。”
“爸。”刘承喊了一声,声音里的情绪被他极力压着。
“嗯。”刘建国应了一声,目光在儿子脸上停顿了一秒,似乎察觉到他今天有点不同,但也没多问,重新拿起了报纸。
这就是他的家。父亲刘建国,市机械厂的老技术工人,话不多,严肃,有点老派,但对家庭极有责任感。母亲李素珍,以前是纺织厂的女工,厂子效益不好下岗后,就在家操持家务,偶尔接点零活补贴家用,性格温和坚韧,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这个家和儿子身上。
普通,甚至有些清贫,但却是他两世灵魂唯一的锚点。
饭菜的香气从厨房里一阵阵飘出来,是记忆里最温暖的味道。母亲在厨房和客厅之间忙碌穿梭,嘴里念叨着:“承承,快去洗手,今天小酥肉炸得特别脆!老刘,别看了,帮忙摆碗筷……”
父亲“唔”了一声,放下报纸,起身去厨房拿碗筷,动作不紧不慢。
刘承站在客厅中央,看着这一幕,鼻腔酸涩得厉害。他用力眨了眨眼,把那股湿意逼了回去。
真好。
还能这样,真好。
吃饭的时候,李素珍不停地给刘承夹菜:“多吃点,学习累,得补补。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功课跟得上吗?”
“挺好的,妈。”刘承埋头吃饭,含糊地应着,椒盐小酥肉外酥里嫩,是他记忆里的味道,分毫不差。
刘建国吃饭很快,但很安静,偶尔抬眼看看儿子,问一句:“上次说的物理竞赛,准备得怎么样了?”
“在准备。”刘承回答。他记得确实有这么个竞赛,前世他拿了省二等奖,让父母高兴了很久。
“嗯,尽力就好。”刘建国说完,又继续吃饭。
饭桌上的话题琐碎而平常,母亲的唠叨,父亲的沉默,都让刘承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宁。他甚至有点享受这种被“管着”的感觉。
直到李素珍像是突然想起什么,说道:“对了,老刘,我听楼下张姐说,她们家孩子回来说,今天学校广播里,有个学生念了首什么诗,闹出好大动静,说是写得特别好,叫什么……《将进酒》?承承,你听说了吗?”
刘承夹菜的动作顿了一下。
刘建国也抬起了头,看向儿子,眼神里带着询问。
刘承把一块小酥肉放进嘴里,慢慢嚼着,咽下,然后才抬起头,迎上父母的目光,语气尽量平淡地说:“嗯,听说了。那诗……是我念的。”
“啪嗒。”
李素珍手里的筷子掉在了桌上。
刘建国拿着饭碗的手僵在了半空,那双沉稳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清晰的、毫不掩饰的惊愕。
客厅里,只剩下老旧冰箱运作时嗡嗡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