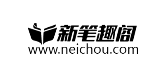无忧阁三楼,独孤修专属的房间里,炭盆烧得正旺,驱散了窗外的寒意。
独孤修、杨广,还有特意请来的越国公杨素围坐在一起,桌上摆着几碟小菜和一壶温好的酒,气氛却不像吃饭那么轻松。
“时机差不多了。”独孤修抿了口酒,悠悠地说。他手里把玩着一枚“无忧牌”,目光却看向杨广和杨素。
“皇后病体渐愈,陛下心神稍定。这个时候,该让咱们的太子殿下,再给大家表演个‘节目’了。”
杨广眼神一凝:“舅舅的意思是?”
“咱们这位太子爷,最近日子过得挺滋润啊。”
独孤修嘴角扯出一丝嘲讽的笑,“母后病着,他心里估计也不怎么痛快,总得找点乐子排解排解吧?我听说,东宫新排了一出歌舞,太子殿下甚是喜爱,几乎夜夜笙歌,还与那云昭训等人,饮酒作乐,常常通宵达旦。”
杨素捋着胡须,眼中精光一闪:“此事,老夫亦有耳闻。只是……宫闱之内,若非亲眼所见,难以作为凭证。”
“谁说需要凭证了?”独孤修放下酒杯,“我们只需要让‘该看的人’,在‘恰当的时候’,看到那么一点点就够了。实事求是!我们绝不做故意构陷、栽赃嫁祸、无中生有的脏活。证据?那是陛下和御史台该操心的事。”
他看向杨广:“还记得咱们后援会里,那个他爹是谏议大夫,跟太子太傅忠孝王爷伍建章关系莫逆的小子吗?”
杨广立刻想了起来:“刘御史家的二郎?他爹性子耿直,最重礼法规矩。”
“对,就是他。”独孤修点点头,“让他‘偶然’发现点事情。不用他做什么,只要把他看到、听到的,原原本本告诉他爹就行。剩下的事,那位耿直的刘御史,自然会知道该怎么做。伍建章老夫子,也绝不会坐视不理。”
计划悄无声息地展开了。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东宫内却是灯火通明,丝竹管弦之声隐隐传出宫墙。
太子杨勇心情似乎不错,连日来因母后生病而积压的烦闷,似乎都要在今晚宣泄出来。他坐在上首,宠妾云昭训依偎在旁,下面坐着几个善于逢迎的东宫属官和伶人。殿中舞姬翩翩起舞,酒香四溢,一派奢靡享乐景象。
酒至半酣,杨勇已是醉眼朦胧,拉着云昭训的手,高声谈笑,言语间已有些失态。一个伶人为了讨好,说了些近乎谄媚、有失体统的笑话,引得杨勇哈哈大笑,竟还给予了赏赐。
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东宫外围的一处偏殿廊下,一个穿着普通内侍衣服的年轻人,正借着阴影的掩护,屏息凝神地听着里面的动静。
他是刘二郎。
刘二郎是靠着后援会信息组搞来的东宫内部粗略地图,和某个被银钱“打动”的小太监的掩护,混进来“长见识”的。
他听到里面传出的淫词艳曲和太子的放浪笑声,他脸上露出鄙夷和兴奋交织的神色。
等见识长得差不多了,他不敢久留,确认了里面的情况后,便悄无声息地溜走了。
第二天一早,刘御史府上。
刘二郎“恰好”在父亲书房外听到父亲与老友伍建章唉声叹气,议论太子近来疏于学业,担忧其德行。他立刻“义愤填膺”地进去,将自己昨晚“偶然”路过东宫外墙时听到的“些许”动静,“如实”禀报给了父亲和伍太傅。
“父亲,伍世伯,孩儿昨夜……昨夜路过东宫外,听得里面……里面笙歌不绝,似乎……似乎还在饮酒,更有……更有不堪之语传出……”刘二郎说得吞吞吐吐,脸上恰到好处地带着惶恐和愤慨。
刘御史和伍建章一听,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伍建章更是气得胡子直抖,他一生致力于教导太子,恪守礼法,如今听到太子在母后病中竟如此荒淫无度,简直如同被人当面打了一巴掌。
“荒唐!无耻!”伍建章猛地一拍桌子,老泪瞬间涌出,“国母尚在病中,身为储君,不思忧心侍疾,反而在宫中饮宴作乐,狎昵伶人,行此……行此失德之事!老夫……老夫教储无方,有何面目立于朝堂!有何面目见陛下!”
他越说越激动,最后几乎是捶胸顿足。
刘御史也是面色凝重,他拉住伍建章:“伍公息怒!此事……此事关系国体,绝不能姑息!明日早朝,我定要据实奏报陛下!” 翌日,麟德殿。 殿内气氛庄重肃穆。就在朝会议程快要结束时,谏议大夫刘御史猛地出列,手持象笏,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 “陛下!臣要弹劾太子殿下!” 一语既出,满殿皆惊。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刘御史和脸色骤变的太子杨勇身上。 隋文帝杨坚的眉头也立刻皱了起来,沉声道:“讲!太子有何过失?” “臣闻,就在三日前,皇后娘娘凤体尚未痊愈之际,太子殿下于东宫内,召集伶人宠妾,彻夜饮宴,笙歌达旦!席间言行放浪,赏赐无度,全然不顾母后病体,不念储君身份,行止失当,有亏德行!此乃臣与太子太傅伍建章大人,共同查实!”刘御史豁出去了,声音洪亮,字字清晰。 他话音刚落,白发苍苍的伍建章也颤巍巍地出列,直接跪倒在地,涕泪交加,以头抢地: “陛下!老臣有罪!老臣教储无方,致使太子殿下德行有亏,竟于国母病中行此荒唐之事!老臣愧对陛下,愧对皇后,愧对天下臣民!恳请陛下严惩老臣,并……并严加管束太子,以正视听,以肃宫纪啊!”他哭得情真意切,让人动容。 太子杨勇站在队列前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又惊又怒,他想要辩解,却一时语塞,因为刘御史所说,基本是事实,只是细节上可能有些夸张。他求助般地看向高颎。 高颎此刻的脸色也是难看至极。 他没想到太子竟然如此不谨慎,在这种敏感时期被人抓住了如此确凿的把柄。 他心中虽然极其恼怒太子的不成器,但此刻也必须维护。朝堂的争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他深吸一口气,出列奏道: “陛下,刘御史、伍太傅所言,或许……或许有其事。然,太子殿下年轻,或是一时烦闷,偶有失检。况且,宫闱之事,外人难以尽知详情。依老臣之见,不宜过分苛责,小惩大诫即可……” 他这话,明显是在和稀泥,试图将大事化小。 然而,还没等杨坚表态,站在武将队列里的宇文述冷笑一声,出言讥讽道:“高相此言差矣!储君乃国之根本,德行岂是小事?‘偶有失检’?在皇后病中饮宴作乐,这若是‘失检’,那何为‘有德’?莫非高相以为,此等行径,合乎礼法吗?” 他直接将高颎的话顶了回去,语气尖锐。 高颎被噎了一下,脸色更加难看,但他城府极深,知道此时再争辩只会更糟,于是选择了沉默,只是那紧抿的嘴唇显示了他内心的不平静。 龙椅上的杨坚,看着下方跪地痛哭的老臣伍建章,看着脸色惨白、无言以对的太子,又想起卧病在床的皇后和近日杨广夫妇的“至孝”表现,一股怒火直冲头顶。 他猛地一拍御座扶手,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逆子!” 一声怒喝,震得整个大殿鸦雀无声。 杨坚指着太子杨勇,气得手指都在发抖:“你……你母后尚在病中,你不知忧虑,不思尽孝,反而在宫中纵情声色,荒淫无度!你还有没有一点为人子的良心!还有没有一点储君的体统!” “父皇息怒!儿臣……儿臣知错了!” 杨勇吓得魂飞魄散,噗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叩头。 “知错?朕看你是屡教不改!”杨坚怒不可遏,“传朕旨意!太子杨勇,行为失检,德行有亏,即日起,闭门读书思过,非朕诏令,不得出东宫半步!一应政务,暂由晋王杨广代为处理!退朝!” 说完,杨坚根本不给任何人再说话的机会,拂袖而去,留下满殿噤若寒蝉的百官,以及面如死灰、瘫软在地的太子杨勇。 朝堂之上,支持太子的官员们面面相觑,如丧考妣。 而杨广一系的官员,虽然竭力保持着表面的平静,但眼神中的兴奋和激动却难以完全掩饰。 高颎站在原地,看着被内侍搀扶起来的太子,又看了一眼面色平静、眼底却藏着锋芒的杨广,心中一片冰凉。 他知道,经此一事,太子的声望跌入了谷底,而晋王的势头,已经再也无法阻挡了。这场夺嫡之争的天平,伴随着皇帝那声“闭门思过”和“政务交由晋王处理”的旨意,发生了决定性的倾斜。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出两仪殿,自然也传到了无忧阁。 独孤修听着明月的汇报,只是淡淡地笑了笑,继续翻看着手里那本关于漕运河道水文记录的旧书。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接下来,该考虑怎么帮杨广把这“代为处理”的政务,处理得漂漂亮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