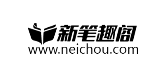第三章 织网
陈远将宋阁老独子从诏狱捞出那夜,京城落了薄雪。
宋府管家躬身递来名帖:“老爷说,陈主事日后若回余姚,务必过府一叙。”
陈远没收名帖,只问:“听闻贵府藏书楼有套孤本《洗冤录》?”
三日后,宋府送来三车旧书,夹着一份浙江官员考绩密档。
他不动声色,在卷宗空白处批注律条,借书吏赵五之手传遍刑部。
当周文斌怒斥他“收买人心”时,陈远翻开《大明律》:
“大人,下官只是依律办事。”
窗外,新来的书吏张岱,默默记下这一幕。
…
诏狱深处渗出的寒气,比刑部甬道里更重百倍,混杂着铁锈、腐肉和绝望的腥臊,几乎凝成实质,沉甸甸地压在陈远胸口。引路的锦衣卫小旗官姓钱,一张脸像冻僵的石头,只在腰间绣春刀的刀柄上,五指习惯性地摩挲着,发出细微的皮革摩擦声。幽暗的火把光跳跃着,将两侧铁栅栏后蓬头垢面、形销骨立的影子拉扯得如同鬼魅,空洞麻木的眼神偶尔掠过火光,又迅速隐没在更深的黑暗里。锁链拖地的哗啦声、压抑的呻吟和不知何处传来的、令人牙酸的刑具转动声,是这里永恒的背景。
“就这儿了,陈主事。”钱小旗在一间格**冷的牢房前停下,声音干涩,不带丝毫感情。他掏出钥匙,插入那把巨大、锈迹斑斑的铁锁,用力一扭,“咔哒”一声,在死寂的通道里格外刺耳。
铁门被拉开,一股浓烈的、混合着血腥、呕吐物和霉烂稻草的恶臭猛地扑出来。陈远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借着钱小旗手中火把摇曳的光,看清了角落里蜷缩着的人影。
那几乎已不成人形。一身华贵的湖绸袍子被撕扯得破烂不堪,沾满污秽和暗褐色的血痂。头发散乱地粘在青紫肿胀的脸上,嘴角破裂,一道干涸的血痕延伸到下颌。他紧紧抱着双臂,蜷缩在冰冷潮湿的稻草堆里,身体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着,喉咙里发出断续的、如同幼兽濒死般的呜咽。唯有那双勉强睁开一条缝的眼睛里,还残留着一点属于活人的、被巨大恐惧碾碎的光——那是宋时襄,前内阁次辅、帝师宋濂的独子。
陈远的心猛地一沉。这伤势,绝非寻常斗殴或拒捕所致,分明是下了死手!他上前一步,蹲下身,尽量放轻声音:“宋公子?宋公子?下官刑部浙江司主事陈远,奉部堂之命,提你过堂。”
宋时襄的身体猛地一颤,像受惊的兔子般拼命向后缩,眼神涣散,口中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不是我……真不是我……我不知道……别打我……”声音嘶哑破碎,充满了极致的恐惧。
陈远的目光锐利如鹰隼,迅速扫过他裸露在外的皮肤。脖颈、手臂、肋下……那些青紫肿胀的伤痕边缘,隐隐透出指印的轮廓!这分明是刻意殴打、逼供留下的痕迹!一股冰冷的怒火瞬间窜上陈远心头,但他面上依旧沉静如水。他站起身,转向一旁如同石雕般伫立的钱小旗,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
“钱大人,宋公子伤势沉重,神志已然不清。依《大明律·刑律·断狱》‘应议之人不合拷讯’条,凡应议(八议)之人,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宋阁老乃三朝元老,帝师之尊,宋公子属‘议贵’之列!尔等私刑拷掠,已属违律!若再延误救治,致其有失,这干系,恐怕不是你一个小旗能担得起的!”
“违律”二字,像两记重锤砸在寂静的通道里。钱小旗那张冻僵的脸上,肌肉几不可察地抽搐了一下。他摩挲刀柄的手指骤然停住,眼神深处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陈远的话,精准地戳中了要害。宋时襄的身份太特殊,宋濂虽已致仕归乡,但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余威犹在。真在诏狱里被弄死弄残了,上面为了平息物议,丢出几个替罪羊是必然的。他一个小旗,首当其冲!
钱小旗喉结滚动了一下,终于不再是无动于衷的石像,声音干巴巴地响起,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退让:“陈主事言重了。此人……是拒捕时自己跌撞所致。不过……”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地上抖成一团的宋时襄,“既然部堂有令提审,自然要活的。来人!把他架起来!”
两个如狼似虎的锦衣卫力士上前,粗暴地将瘫软的宋时襄拖拽起来。宋时襄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几乎昏厥过去。
“慢!”陈远抬手阻止,语气不容置疑,“宋公子伤重,岂能如此拖拽?去找副担架来!要快!若再伤上加伤,谁也担待不起!”他的目光紧紧锁住钱小旗,寸步不让。
钱小旗的脸色变幻了几下,最终在陈远那平静却蕴含着巨大压力的目光下,朝旁边一个力士使了个眼色。那力士犹豫了一下,转身快步消失在通道的黑暗中。不多时,一副简陋的担架被抬了过来。
当陈远亲自指挥着两个还算稳妥的刑部差役,小心翼翼地将昏沉沉的宋时襄抬出诏狱那扇如同地狱之口的沉重铁门时,外面清冷的夜风裹挟着细碎的雪沫迎面扑来。他深深吸了一口这冰冷却干净的空气,仿佛要将肺腑中积郁的浊气尽数涤荡干净。回望身后那高耸、沉默、如同巨兽蛰伏般的诏狱轮廓,陈远眼中寒光一闪即逝。他侧过头,对身边一个面相忠厚、一直沉默跟随的刑部老差役低声道:“老赵,你亲自带人,将宋公子稳妥送至太医院。告诉值守太医,就说刑部浙江司陈主事请他们务必尽心诊治,所需用度,暂记在我名下。此间事,莫要多言。”
老差役赵五,是陈远这几个月在刑部底层默默观察后,唯一觉得尚存一丝良知、且口风甚紧的老吏。赵五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无声地点了点头,招呼同伴,抬起担架,迅速消失在风雪弥漫的夜色中。
陈远回到刑部浙江司签押房时,已是后半夜。值夜的书吏趴在案上打盹,鼾声轻微。陈远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无声息地坐回自己冰冷的公案后。桌上,一份关于宋时襄案初步勘问的“行文”静静躺着——这是钱小旗那边匆匆递过来的,自然是“醉酒滋事,拒捕伤人”的调子。陈远提笔蘸墨,在那份漏洞百出的行文上,并未直接驳斥,而是以刑部主事复核的名义,在每一处关键疑点旁,用蝇头小楷清晰、冷静地批注上引用的《大明律》条文。
“……伤者供述前后矛盾,无旁证佐证其‘拒捕’之词,依《大明律·刑律·诉讼》‘诬告’条及‘佐证不实’条,此证存疑……”
“……宋时襄身无寸铁,所控‘夺刀伤人’与现场遗留凶器形制、其本人伤势位置皆不合常理,依《洗冤录·斗殴篇》,当详查……”
“……诏狱提人,未按规附‘伤情单’,不合《刑部则例》,依《大明律·刑律·断狱》‘检验不实’条,须补录详报……”
墨迹干透,他将这份批注得密密麻麻的行文,轻轻放在案头最显眼的位置,确保明日第一个来当值的书吏一眼就能看到。然后,他吹熄了油灯,在冰冷的黑暗和远处诏狱隐约传来的哀嚎声中,和衣躺在了那张硬板床上。身体疲惫到了极点,意识却异常清醒。宋时襄那双被恐惧碾碎的眼睛,诏狱通道里钱小旗那瞬间的慌乱,如同走马灯般在眼前旋转。这张网,终于被他撕开了一个极其微小的口子。代价,是他彻底将自己暴露在了更猛烈的风暴眼边缘。
三天后,一个雪霁初晴的午后。陈远刚从刑部那扇乌沉沉的大门走出来,便看到一辆青呢小车安静地停在斜对街的巷口。车辕上坐着一个穿着半新不旧棉袍、面容精干的老者,正是宋府那位沉默寡言的管家。见陈远出来,老者利落地跳下车辕,快步迎上,动作沉稳,毫无寻常家仆的谄媚之气。他在陈远面前一步处站定,双手捧着一张泥金名帖,深深一躬,腰弯得极低,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陈主事大恩,宋府上下没齿难忘。老爷在余姚听闻此事,特命老奴前来致谢。老爷说,”他微微抬起眼,目光沉静地直视着陈远,“陈主事年少有为,心系律法,实乃国之栋梁。他日若荣归故里,途经余姚,务请拨冗过府一叙,容老朽略尽地主之谊。”
那张泥金名帖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柔和内敛的光泽,“宋濂”二字力透纸背,仿佛蕴含着千钧之力。这是来自一位致仕阁老、帝师的橄榄枝,其分量,足以让京城无数五品以下的官员心跳加速。
陈远的目光在那名帖上停留了一瞬,眼神平静无波。他没有伸手去接,反而微微侧身,避开了老管家这一礼,声音温和却带着一种疏离的客气:“宋管家言重了。下官奉部堂之命行事,职责所在,不敢居功。宋阁老德高望重,乃我辈楷模。下官位卑职小,岂敢叨扰老大人清静?”他顿了顿,话锋轻轻一转,语气自然得如同闲话家常,“倒是听闻宋阁老归隐林泉后,藏书甚丰,尤以一套前朝孤本《洗冤录》为镇宅之宝?下官于刑名一道,尚在摸索,对此类典籍心向往之,只恨无缘得见。”
老管家捧着名帖的手几不可察地微微一滞。他抬起眼,再次深深看了陈远一眼。眼前的年轻人,官袍半旧,面容清癯,眼神清澈坦荡,不见半分对权势名帖的热切,只有提到《洗冤录》时,才流露出一种纯粹的、读书人式的向往。老管家纵横宋府数十年,阅人无数,此刻心中却也不由得暗赞一声:好定力!好心思!
他缓缓收回了名帖,脸上露出一丝真正温和的笑意,语气也多了几分亲近:“陈主事果然风雅。老爷确实藏有那套书。既蒙主事垂询,老朽回去便禀明老爷。想必老爷知晓主事此等雅好,亦会欣然。”
两人又寒暄几句,老管家便告辞登车而去。青呢小车碾过薄雪覆盖的石板路,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街角。
陈远站在原地,目送马车消失。清冷的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名帖上淡淡的檀香气息。他拢了拢衣袖,指尖在袖中那枚冰冷的刑部主事铜牌上轻轻摩挲了一下,转身汇入长街的人流。那张名帖的分量,他心知肚明。但此刻接下,无异于在身上贴了一道催命符。他要的,不是一道金光闪闪的护身符,而是一把藏在书匣里的钥匙,一把能打开宋阁老那庞大而隐秘人脉网络的钥匙。
三日后。刑部浙江司签押房依旧弥漫着那股熟悉的、混杂着墨臭和阴冷的气息。周文斌昨夜似乎又宿醉,此刻正歪在里间的软榻上,鼾声如雷。几个书吏埋头抄写,大气不敢出。
一阵沉重的车轮碾压石板的声音由远及近,打破了签押房死水般的沉寂。声音在门口停下。紧接着,两个穿着宋府号衣的健仆抬着一个沉甸甸的樟木书箱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两个小厮,合力推着一辆堆满书籍的板车,最后一个小厮手里还抱着一个半人高的青布包袱。
“敢问哪位是陈远陈主事?”为首的健仆声音洪亮,眼神在签押房里扫视。
所有人的目光都惊疑不定地投向了角落里的陈远。陈远放下笔,站起身,神色平静:“在下便是。”
那健仆立刻躬身行礼:“陈主事安好!奉我家老爷之命,特将府中一些闲置旧书送来,供主事翻阅。老爷说了,主事乃真正读书种子,这些书在主事手中,强过在库房里蒙尘发霉。”他指挥着仆役将书箱和板车上的书搬到陈远案头旁的空地上。书箱沉重,落地时发出闷响;板车上的书堆得像小山,大多是些经史子集、地方志乘的旧刻本,散发着陈年的墨香和淡淡的樟脑气息。
当那小厮将那个半人高的青布包袱轻轻放在书堆顶上时,陈远的目光似不经意地扫过。包袱皮的一角微微掀开,露出里面书籍的封面一角——赫然是几册纸张发黄、装帧古旧的《洗冤录》!而就在那几册《洗冤录》的下方,隐约可见一个扁平的、用普通黄麻纸包裹的方形物件,与周围书籍的形制格格不入。
“有劳诸位。”陈远拱手致谢,语气真诚。
健仆还礼,带着人干脆利落地退了出去,留下签押房内一片死寂和一座突兀的书山。所有书吏都停下了笔,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堆积如山的书籍,又看看一脸平静的陈远,眼神复杂难明。里间的鼾声不知何时停了。周文斌顶着一头乱发,脸色阴沉地站在里间门口,看着那座书山,又看看陈远,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刻薄话,但最终只是从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猛地甩上了里间的门。
陈远仿佛没看见周文斌的怒气,也没在意那些探究的目光。他走到书堆前,先是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几册孤本《洗冤录》,珍重地拂去封面上的微尘,放在自己案头最顺手的位置。然后,他才开始整理其他的书籍。他动作不疾不徐,一本本拿起,拂拭灰尘,分门别类地归置到墙角临时清出的空架上。
当他拿起那个半人高的青布包袱时,手指几不可察地在包袱底部那个用黄麻纸包裹的方形物件上轻轻一按。触手微硬,边缘方正。他神色如常,解开包袱皮,里面果然是一摞普通的县志和文人笔记。他随手将这几本书也归置到书架上,那个黄麻纸包裹的物件,则被他不动声色地混入了一堆待处理的旧档文书中,毫不起眼。
直到签押房里只剩下他一人整理书籍的窸窣声,他才重新坐回公案后。案头,摊开着一份需要他复核的、关于地方上报的一桩普通田土纠纷案卷宗。他提起笔,蘸了墨,却没有立刻批阅。
他的目光落在卷宗空白处。这份卷宗本身并无太大问题,但卷中引用的地方“土例”与《大明律·户律》中关于“典卖田宅”的条文,存在一处极其细微的冲突。这种冲突,地方官往往睁只眼闭只眼,刑部复核时也多是一笔带过。
陈远沉吟片刻,笔尖悬在空白处。他没有直接批驳地方官,而是以清晰工整的小楷,在卷宗旁引用了《大明律》的原文,并详注了前后律条的关联和解释,最后以一句平实却有力的疑问作结:“……此‘土例’与律文相左,其效力几何?是否当以律为准绳,以正视听?请上官明鉴。”
批注完毕,他轻轻吹干墨迹。恰好此时,书吏赵五抱着一叠新到的公文走了进来。赵五放下公文,目光习惯性地扫过陈远案头,看到了那份批注过的卷宗。
“陈主事,这份是……”赵五低声询问。
“哦,是南直隶句容县上报的一桩田土旧案,有些律条上的疑问,我批注了几笔。”陈远语气随意,将卷宗拿起,递给赵五,“劳烦赵书吏,按程序先归档吧。若周大人问起,便说下官有些浅见,附在卷后了。”
赵五接过卷宗,目光下意识地落在陈远那清晰详尽的批注上。他识字不多,但长期在刑部,对律条也略知一二。陈远引用的律文和那句平实有力的疑问,像一道微弱却清晰的光,刺破了他心中长久以来对地方“土例”模糊不清的认知。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亮光,低声应道:“是,小的明白。”他捧着卷宗,脚步似乎比往日轻快了一分,走向存放文书的柜架。
接下来的日子,陈远案头需要复核的卷宗,总会“恰好”地夹杂着一些涉及律法疑点、或地方官处置模糊的案子。他批阅得异常认真,在卷宗空白处留下的批注也越来越多。有时是引经据典,阐释律条本义;有时是层层推演,指出地方官判词中的逻辑疏漏;有时则只是提出一个基于律法精神的疑问。他的批注从不越权指摘上官,也从不带个人情绪,字字句句都紧扣律法条文,严谨得像在雕琢一件器物。
这些被精心批注过的卷宗,总会“顺理成章”地经由赵五的手,流转到签押房其他书吏,乃至其他清吏司的低层官吏手中。起初,无人注意。渐渐地,开始有人私下议论。那些清晰有力的律条引用,那些一针见血的疑问,如同投入死水的石子,在刑部底层这些终日埋首案牍、早已麻木的书吏和小官心中,激起了微澜。
“……陈主事这注解……引的是《名例律》的‘断罪引律令’条吧?说得在理啊,咱们断案,可不就得依着律条来么?”
“……你看他批这桩‘斗杀’案,地方上只提‘事出有因’,他直接引了《刑律》‘斗殴及故杀人’条,问这‘因’是否构成‘故’?这问得……让人没法糊弄啊!”
“……听说没?昨日周郎中想驳他批的一份卷子,结果陈主事当场翻出《大明律》和《问刑条例》,一条条对着讲,愣是让周郎中哑口无言!啧啧……”
这些低语,如同细微的溪流,在刑部这座庞大官僚机器的底层缝隙里悄然流淌、汇聚。一种微妙的、难以言喻的变化,在无声地发生。当书吏们再接到需要陈远复核的卷宗时,眼神里少了几分麻木,多了几分不易察觉的审慎。当陈远偶尔就某个律条问题询问时,开始有人小心翼翼地、带着一点被认可的激动,说出自己的见解。赵五在整理文书时,腰杆似乎挺直了一些,看向陈远的背影时,眼神里也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敬意和归属感。
这一日,陈远刚将一份批注详尽的卷宗递给赵五。卷宗里,他针对一桩地方豪强侵占民田、官府判罚畸轻的案子,不仅引用了《户律》和《刑律》相关条文,更在批注末尾,看似不经意地提了一句:“……此案所涉余姚县田亩纠纷,其地界划分,似可参考嘉靖二十一年版《余姚县志·舆地卷》所载图示……”
赵五接过卷宗,正要转身,里间的门“哐当”一声被猛地拉开!周文斌怒气冲冲地闯了出来,脸色铁青,显然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他几步冲到陈远案前,指着案头那堆积如山的宋府送来的书籍,又指向赵五手中那份刚批注好的卷宗,声音因为暴怒而尖利刺耳:
“陈远!你好大的胆子!弄这些破书堆满公堂,装什么风雅?!还有你!”他猛地转向赵五,唾沫横飞,“整天捧着这些被他涂涂抹抹的破纸到处晃荡!怎么?他陈主事批注过的,就是金科玉律了?你们一个个的,是不是都被他收买了?!想在这浙江司另立山头不成?!”
签押房里瞬间死寂。所有书吏都吓得面如土色,噤若寒蝉。赵五捧着卷宗的手微微发抖,脸色发白,却咬着牙没有后退。
陈远缓缓站起身。他没有看暴跳如雷的周文斌,而是走到自己案头,拿起那本始终摊开、已被他翻得卷边的《大明律》。他翻开书页,动作沉稳,指尖精准地找到其中一页,然后双手捧起,将翻开的书页稳稳地推向周文斌的方向。
他的声音不高,甚至带着一丝下级官员应有的谦恭,却字字清晰,如同金玉相击,在死寂的签押房里回荡:
“周大人息怒。下官岂敢收买人心?更不敢另立山头。下官所做,不过恪守本分,依律办事而已。”
他微微一顿,目光平静地迎上周文斌那双几乎要喷出火来的眼睛,手指轻轻点在书页上那几行墨色浓重的律文上:
“大人请看,《大明律·吏律·公式》‘事应奏不奏’条有载:‘凡军官犯罪……若文职官有犯,奏闻请旨,不许擅自勾问。’此乃律法明文,纲纪所在。下官批注卷宗,所引所疑,皆出于此律,出于此典,不敢有丝毫逾越。若下官依律复核、详加批注便是‘收买人心’、‘另立山头’,那敢问大人,”
陈远的声音陡然拔高了一分,带着一种凛然的力量:
“置这煌煌《大明律》于何地?!置我大明刑部职司于何地?!”
“你……!”周文斌被这突如其来、引经据典的反问问得一时语塞,指着陈远的手指气得直抖,脸色由青转紫,如同被掐住了脖子的公鸡。他张着嘴,想咆哮,想怒斥,却发现自己竟找不到一句在律法条文上能站住脚的话来反驳!陈远的每一句都钉在《大明律》上!他只能徒劳地喘着粗气,从喉咙里挤出破风箱般的声音。
整个签押房落针可闻。所有书吏都低着头,肩膀却几不可察地微微挺直了一些。赵五捧着卷宗的手,不再颤抖。
就在这时,签押房门口光线一暗。一个穿着崭新青色官袍、面容尚带几分书卷气的年轻人,捧着一叠文书,有些拘谨地站在门口。他是新分到浙江司的书吏,名叫张岱,寒门出身,刚通过吏部铨选。
他显然撞见了方才这剑拔弩张的一幕,脸上带着一丝惊愕和茫然,目光在暴怒的周文斌和手捧《大明律》、神色平静如渊的陈远之间来回逡巡。最终,他的目光落在了陈远手中那本翻开的律书上,又飞快地扫过赵五手中那份批注详尽的卷宗,眼中闪过一丝复杂而明亮的光芒。
陈远的目光似乎不经意地掠过门口的张岱,随即收回,重新落回气得浑身发抖的周文斌身上。他微微躬身,姿态依旧恭敬,语气却已恢复了平日的沉静:“大人若无其他训示,下官继续复核卷宗了。”说罢,他从容地坐回座位,拿起笔,仿佛刚才那场风暴从未发生。
周文斌站在原地,胸膛剧烈起伏,脸色变幻不定,最终狠狠一跺脚,像一头斗败的公牛,转身冲回了里间,重重摔上了房门。
签押房里,只剩下书吏们重新响起的、却似乎比往日轻快了些的沙沙书写声。窗棂透进来的光线,落在那座由宋府送来的旧书堆成的小山上,也落在那本静静摊开在陈远案头的《大明律》上。陈远蘸了墨,在摊开的公文纸上,继续书写着。笔尖沉稳,墨迹清晰。
无人注意的角落,新来的书吏张岱,默默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他没有立刻开始抄写,而是从怀中摸出一本磨破了边的《大明律》小册子,轻轻翻开,目光在陈远方才引用的那条律文上停留了许久,然后,在旁边空白处,用极细的笔尖,用力写下了一个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