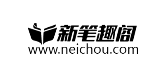我揣着舅舅五年前从景明国寄来的信,手里攥着阿爷塞的那把弯刀。刀鞘是枯陀国的老牛皮,磨得发亮,贴在掌心能觉出细微的纹路——就像阿爷手掌的茧,粗糙却暖。他往我怀里塞刀时,胡茬蹭着我耳朵:“你舅舅当年带走它,我就说过,刀能砍柴,也能记着,好东西不分邦国。”
其实我对舅舅的记忆,大半是戈壁上的风与笑声。他没去景明国前,总爱在枯陀国的沙地里教我认种子。有次他从昌宁国商人那换了包南瓜籽,说“这东西埋在沙里能长出手掌大的瓜”,阿爷骂他“异想天开”,他却拉着我在屋后挖了个坑,埋籽时特意往土里掺了把碎羊毛:“瓜也怕冷,给它盖点被子。”
那阵子他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破了边,却总爱卷到胳膊肘,露出小臂上的疤——不是后来被马蹄蹭的那道,是年轻时为了救被流沙困住的昌宁国商人,用刀割破手放血做标记留下的。他说那商人教他“沙子会骗人,但根不会”,所以他总带着把小铲子,见着陌生的草就挖出来看根须,说“知道根什么样,就知道这东西能不能活”。
有年春天,他不知从哪弄来架小水车,不是景明国那种笨重的,是用枯树枝和羊皮缝的,就巴掌大。他举着在太阳底下转,水珠被甩出来,像撒了把碎星星。“你看,”他指着水珠在沙地上洇出的小坑,“水不用多,找对法子就能留住。”那天我们用这小水车浇活了三棵快枯死的杨树苗,他蹲在树苗旁,用刀在树干上刻了个小小的狼头,说“等你长到能遮荫,我就带你去景明国看大水车”。
那时的风刮过戈壁,都带着草木的腥气。他总说“好东西不分邦国,就像这南瓜籽,到了枯陀国也能结果”,说这话时,他眼里的光比狼图腾的铜钉还亮——我原以为,景明国的青石板路上,也该有这样的光。
景明国的都城真大,路是青石板铺的,被千万双脚磨得光溜,光脚走在上面,凉丝丝的硌得慌。我按着信上的地址找南坊,青石板的缝里嵌着碎布片、瓜子壳,还有半枚生锈的铜钱。问了个戴瓜皮帽的老头,他帽檐压得低,露出的下巴上有颗痣,瞥我腰间弯刀时,嘴角撇得像被风刮过的草:“南坊?早不是你舅舅的地界了。”拐杖在石板上敲了敲,“咚”的一声,惊飞了檐下的麻雀。
巷子尽头围了好多人,像堵墙。我挤进去,心口猛地被什么攥住了——木柱子被晒得发烫,舅舅的灰布短褂黏在背上,汗渍晕成大片深色,像被雨打湿的土块。他左颧骨上那块疤,信里提过是赶车时被马蹄蹭的,此刻在日头下泛着油亮的红,那是我小时候总摸的地方,当年他用这道疤蹭我的脸,说“男人的疤是勋章”,此刻却被麻绳勒得变了形,紫红的印子陷进皮肉里。
京兆府的衙役正想夺他别在腰间的弯刀,手抓着老牛皮刀鞘,攥出几道白痕。舅舅死死攥着刀柄,指节发白,狼图腾的眼睛处磨得发亮,像在盯着围观的人,又像在看他自己紧抿的嘴角:“这刀救过枯陀国的人,也该救景明国的人!”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却带着股劲,震得周围的哄笑声矮了半截。
人群后缩着个穿青布衫的年轻男人,是工部的画工小秦。他手里攥着张草纸,被汗浸得发皱,上面画的水车草图,三根辐条明显比别的短,墨迹晕开,像被水泡软的麦秆,在他掌心微微发颤。见我看他,他慌忙把纸往怀里塞,脸涨得通红,耳尖却白得像没晒过太阳。
街角“悦来栈”的女掌柜见我呆站着,伸手把我往回拉。她的手带着灶膛的温度,月白布衫的袖口沾着点面碱,是刚洗过碗的味。“先住下,灶上温着粥。”她笑起来眼角有浅浅的纹,像被风拂过的水。端来的小米粥上漂着层油花,碗边搭着双竹筷,筷尾刻着个极小的“周”字,刻痕里还嵌着点陈年的粥渣——后来才知道,那是舅舅的姓,也是她丈夫的姓。
夜里我被地窖的响动惊醒,木梯被踩得“吱呀”响,像有人在磨牙。女掌柜举着油灯往地窖走,菜籽油的烟味混着地窖里的霉味飘上来,呛得人鼻子发酸。她月白布衫的后摆沾着湿泥,是下午去粮仓附近踩的,泥里还裹着半片粟米壳,黄澄澄的,在灯光下泛着光。
地窖里黑得像泼了墨,只有油灯的光圈在动。她打开墙角的木箱,铁锁“咔哒”一声弹开,里面的半截水车辐条带着松木的腥气——那是虫蛀过的木头特有的味,像闷了一冬的粮仓底。“我男人原是工部的木匠,”她用布擦着木牌上的灰,布是粗麻布,擦过木牌上的“偷减三根辐条”,留下些白痕,“和你舅舅一起查水转大纺车案,后来从作坊的房顶上摔下来了,说是‘失足’。”
木箱里还有把卷了刃的凿子,刃口崩了个小豁,像被石头硌过;几张画着齿轮的图纸,边角被虫蛀了些小洞,露出后面的草纸;最底下压着双布鞋,鞋底磨穿了,鞋帮上绣着半朵桃花,针脚歪歪扭扭的——女掌柜说,是她男人临死前,想给她绣朵完整的,没绣完就……油灯的光在她脸上晃,把泪影投在木箱壁上,像片晃动的水。
“那戴瓜皮帽的老头……”我想起他袖管里的木匠尺。
“他儿子原是作坊的学徒,”女掌柜把木牌放回箱子,手指抚过“周”字,竹筷上的刻痕挂住根头发,是她下午梳头时缠上的,黑得像作坊里的墨,“因不肯偷减辐条被赶走,那年冬天就饿死了。老头总说,是昌宁国的水车害了人,却不想想,仿造的人是谁,包庇的人又是谁。”
第二天去给舅舅送水时,路过最大的“丰裕粮栈”,木柜台被算盘珠子敲得咚咚响。穿靛蓝短打的苏二娘正站在柜台后,左手无名指缺了半截,断口处的伤疤在日头下泛白,像块没化的雪。她拨算盘的手快得像翻飞的蝶,算珠是铸铁的,沉甸甸压在紫檀木框上,十年用下来,框子磨出细痕,泛着油亮的光。
“苏二娘,女人家别总摸算盘,学学绣花才是正经!”粮栈门口的王老板叼着烟袋,烟油子滴在青石板上,黑了一小块。
苏二娘头也没抬,断指的手飞快一挑,算珠“啪”地定在“亏空三百石”的位置,声音裹着气,震得周围人耳朵嗡嗡响:“王老板要是闲得慌,不如算算你库房里少的那车米去哪了?去年冬天城西冻死的三个娃,账上可记着你‘捐粮十石’呢。”她从柜台下摸出个账本,纸页发黄,上面的朱砂批注红得像血,“正月十八,你往官府送了两坛酒,换了张‘免查’的条子,我这算盘可都记着呢——连耗羡都算得清清楚楚。”
后来才知,前几日她给舅舅塞过张字条,麻纸糙得像砂纸,上面用朱砂画的粮仓暗格歪歪扭扭却清楚,末尾还加了行小字:“昌宁国匠人带的春麦种,锁在西角地窖,那才是能救景明国的好东西。”——这正是舅舅敢当众喊出“要救景明国”的底气。
舅舅喝水时,喉结动得厉害,像吞着块热石头。他眼里的红血丝像蛛网,缠得人发慌。“你怎么来了?”说的是枯陀国的土话,带着点口音,手往我怀里塞了个东西——是本牛皮封面的小册子,封皮磨得发亮,边角卷成了波浪,里面记着密密麻麻的数字,墨迹有深有浅,想来是换过好几回墨。夹页里藏着张画得歪歪扭扭的地图,上面用枯陀国文字标着“戈壁绿洲”,旁边写着“等外甥来”,笔画里还嵌着点沙粒,是枯陀国的风带来的。
他指尖蹭过地图上的绿洲,粗粝的指腹磨得纸页沙沙响,突然往我手里塞了粒褐色的种子:“昌宁国的耐旱种,我试了两年,城南稻田能长。”种子硬邦邦的,在掌心硌出个小印。我这才注意到,他怀里的衣襟鼓鼓囊囊,摸上去糙糙的,像是藏着把麦种。
两日后,边境传来急报:昌宁国派来的农技匠人团,本想教景明国新的育种法,却因携带“异域种子”被诬陷为“奸细”,双方起了冲突,匠人及随行家眷被赶至城外,成了无家可归的流徙。官府贴出的榜文用了大红纸,墨迹淋漓,“同仇敌忾”四个字大得吓人,贴在城墙上,被风刮得哗哗响。
流徙冲进城那天,衙役正拿铁锁锁粮仓大门。铜锁沉甸甸的,锁芯是黄铜的,磨得发亮,扣在铁环上“咔哒”响。苏二娘突然从粮栈冲出来,靛蓝短褂的下摆扫过门槛,带起一阵麦糠,落在青石板上,白花花的像碎雪。她怀里的铁算盘十年用下来,边角磕出了豁,算珠上刻着的“一”“二”字被磨得浅了,却还能看清。
“哐当!”她抬手就把算盘砸向门锁,铸铁算珠撞在铜锁上,弹起两颗滚到青石板缝里,一颗刻着“五”的珠子蹦到流徙孩子脚边。那孩子约莫五岁,光着脚,脚趾缝里全是泥,捡起珠子就往嘴里塞,硌得牙龈发酸,“哇”地哭了出来。苏二娘突然从怀里摸出颗糖,是去年账上多收的“耗羡”换的,糖纸皱巴巴的,她剥开纸塞进孩子嘴里,断指的手在孩子头上揉了揉,自己也偷偷咬了点糖渣,嘴角沾着点甜。
舅舅趁机站了出去,弯刀在地上划了道线,刀尖挑着那本牛皮册子,纸页被风吹得哗哗响:“不是要抢粮,是要把被锁的种子还给匠人——他们是来教我们种好麦子的!”他怀里的衣襟敞开,露出里面藏着的水车账,封面上写着“林生量”三个字,被摩挲得发亮,像块玉。
衙役举着刀冲过来时,我看见小秦突然疯了似的往工部跑,怀里的草图露了半截,被风掀起个角。可没跑两步就被衙役拦住,刀柄顶在他腰眼上,他“哎哟”一声蹲下去,图纸从怀里滑出来,被衙役踩在脚下,撕得粉碎。有片碎纸飘到我脚边,上面的辐条还能看清,画得细细的,像根没长成的麦秆。衙役踹了他一脚,正踹在腿弯处,他抱着腿蜷缩成一团,很快,裤管就渗出血来,红得像地里的罂粟花。
舅舅没躲,只是把那个抱孩子的昌宁国匠人往身后推了推,用身子护住那本册子。第一刀砍在背上的旧伤处,灰布短褂瞬间洇开块深色,像泼了碗墨;第二刀落在那罐麦灰上,陶罐“啪”地碎了,灰扬起来,像场细雪,落在周围人的脸上,有人打了个喷嚏,有人抹了把脸,手背上沾着点黑。
他倒下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张绿洲地图,边角被血浸透了,红得发黑。我扑过去,见他最后往弯刀的方向看了眼,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种子”。风刮过稻田,废弃的水转大纺车发出“吱呀”声,像谁在哭。
后来官府贴了新榜文,说舅舅“勾结番邦,意图作乱”。红纸上的字被雨水泡得发肿,糊在城墙上,像块烂疮。有人捡起那半块弯刀,看见狼图腾,立刻骂:“果然是番邦奸细的帮凶!”戴瓜皮帽的老头突然冲上去,把木匠尺往那人脸上拍,尺身带着他手心的汗,“啪”地抽在那人嘴角:“这刀救过人!你懂个屁!”人群愣住了,他却突然蹲在地上哭了,手里的尺子沾着不知从哪蹭来的麦灰,抹了满脸。
我和女掌柜偷偷把舅舅埋在城南稻田。挖地时,女掌柜突然说:“去年秋天,他偷偷种的那半亩耐旱麦,收了两袋呢。”她从地窖翻出个布口袋,里面还剩几把麦穗,“他说要留着给你阿爷酿酒,半夜在院子里搓麦粒,笑得像个孩子,麦芒扎了满手也不擦。”铁锹碰着个硬东西——是当年那本被血浸透的水车账,封面上的“林生量”三个字被摩挲得发亮,像块浸了油的木头。我把种子撒在坟头,里面混着女掌柜从粮仓西角摸出的昌宁国春麦种,手指抚过“等外甥来”的字迹。刀柄磕在石头上,发出“当”的轻响,像舅舅当年在枯陀国教我认种子时,用刀背敲石头的声音,脆生生的,能传到老远。
女掌柜蹲下来,往坟上撒了把艾草,青气混着泥土味,呛得人鼻子发酸。她从怀里掏出个旧木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半截被火烧过的农书纸,边缘卷得像波浪;一片水车辐条的碎片,上面还留着个虫蛀的小洞;那双刻着“周”字的竹筷,筷尾的粥渣早已干硬;还有那块没刻完的木牌。“这些,原该是他们哥俩的念想。”她把木盒递给我,手心的温度透过木盒传过来,“带回去,让枯陀国的人知道,景明国也有过想站直的人。”
离开景明国那天,我去辞行。女掌柜正往地窖搬新木箱,松木的箱子散发着清香,箱角露出半截木牌,上面只有一个“等”字,刻痕深得像要嵌进木头里。她袖口沾着新鲜木屑,白生生的,指了指苏二娘的方向——粮栈门口摆了个小摊,苏二娘正给个流徙孩子演示怎么用碎木片算算术,断指的手捏着木炭,在青石板上写得认真,“一”字拉得老长,像根不肯弯的脊梁。
不远处,小秦拄着拐杖路过,右腿还瘸着,裤管空荡荡的,被风灌得鼓鼓的。他想买个苏二娘刻的“准”字木牌,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指尖在布衫上蹭了蹭,像是沾了什么烫人的东西。最终捡起块碎木片,在掌心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对”字,笔画浅得一吹就散。风过时,他忽然瘸着腿走到苏二娘的小摊前,把怀里藏着的半张没撕碎的水车草图(画着完整的、没偷减辐条的样式)悄悄塞到摊位下,草图下还压着半块干饼,是从工部灶房偷偷拿的。苏二娘后来把饼掰给流民,说“是个画工给的”,小秦躲在树后看见,瘸着腿笑了,手在布衫上蹭了蹭,像擦去了层灰。
戴瓜皮帽的老头把木匠尺插在布庄门槛上,尺尖对着粮仓的方向,像在丈量什么。王掌柜还在抠那块狼毒花布料,血珠滴在花瓣上,红得发紫,像朵开错了季节的花,蔫蔫地趴在布面上——官府刚贴了新的封条,写着“通敌嫌隙”,字迹墨黑,盖着京兆府的朱印。
我没回头。走出都城时,青石板路渐渐变成土路,鞋底下沾着的泥越来越沉,带着景明国的土腥味。回到枯陀国,戈壁的风刮在脸上,疼,却痛快,像舅舅当年用刀背拍我后背的力道。
阿爷摩挲着那个木盒,见了竹筷上的“周”字,突然老泪纵横,浑浊的眼泪滴在木盒上,晕开一小片深色。我把那张染血的地图埋在戈壁里,上面压了块石头——石头是从景明国带回来的,沾着点城南稻田的泥,就当舅舅终于回了家。
去年春天,我们试种了舅舅带回来的种子,有枯陀国的耐旱麦,也有昌宁国匠人被没收的春麦种。真的多收了两成粮食,春麦的穗子比本地麦长半指,黄澄澄的像串小月亮。阿爷在田埂上插了块木牌,松木的,上面刻着:“好东西不分邦国”,底下补了行小字:“昌宁国的春麦,枯陀国的土,能长在一起。”牌尾缀着半块磨亮的狼图腾弯刀碎片,风一吹,碎片撞着木牌,“叮咚”响,像在应和。
风过戈壁,牌子呜呜地响,像有人在说:人活着,总得认点真。远处的驼铃叮当响,新的商队来了,这次有昌宁国的匠人跟着,他们手里捧着新的种子,褐的、黄的、白的,像把星星撒在戈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