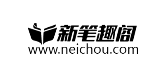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幼吟从浑身剧痛中醒来的时候,脑海里徘徊的,便只有这两句。
自古红颜多薄命,那堪狂风晚来骤雨急!少时爹爹犯事,在御林军撞破自家大门前,横剑自刎。不知情的她和母亲被抓入大狱。出身高门的母亲不堪受辱,在狱中也寻了短见。年仅八岁的她,便被罚入教坊司,历经四年**后,正式出道,做了个抛头露面,卖笑为生的官妓。
买她的,是平安州青雀坊的老鸨冯妈。那年正上京采买女妓。见她小小年纪,虽在大狱里,满脸污浊,却仍掩不住出众的姿容。又兼小时爹爹便请了先生教她琴棋书画,行动间仍颇有一番大户人家千金的风采。便使了银钱让监狱里的人不许动她。待她爹爹的事情落定,便买了她去。
平常大宅院里头,女人间的倾轧便不少,她爹爹又是家里最不受宠的一房。是以她从小便养成了察言观色的本领。因此她虽被没籍充入平安州官妓,略熬了一段时间,便在乐籍中脱颖而出。吹拉弹唱,无一不精。琴棋书画,颇有一番见地。更有一项。
一般官妓,虽然都能口出啼莺之声,都是唱的别人词曲。可幼吟才华出众,多演唱自己填的词。她的词绝少一般妓院爱唱的艳曲淫句,大多歌颂山野自然,语意清新,立意分明,便是一般的秀才举人也没这般娇俏灵动的。颇受那些附庸风雅自诩清高的官老爷们的青眼。又兼她眼色极好,颇会讲那些能令人入心的奉承话。于是为了攀附高官,那些让她去席间应酬的人,颇肯下重金来请。比别个营妓更特别些。
不过两三年,她便声闻千里。便是千里之外的京都中,不少大官也都大略知道她的雅名。
某年,她到京都参加某位上头一时兴起举办的花魁大赛。京都花魁梁娉婷自不待言,夺了状元之名。直隶道花魁李名儿本是探花,但夺了榜眼的幼吟谦让,说更喜探花之名,于是便将李名儿送上榜眼。
幼吟让名之举,本意是忧虑自己名声太胜,怕月满则盈的道理。不想她此举一出,反令京都的文人墨客更为她击节赞赏,道她虽是营妓,却深谙中庸之道。颇有花中之兰的清雅。四花之中,唯有兰花颇受文人青眼。于是一时之间,不论清谈客,甚或达官贵人,反而却更深赏幼吟这株兰花。
一时间,她来京中暂歇的清流坊,客至云来,几乎不曾将门槛踏破。反比状元榜眼处更热闹。原本发愁生意惨淡的老鸨喜出望外。
梁娉婷在京中已是经营许久的人物,官员起落看多了的人,眼界自然宽广。自忖平生穷以应付,已然心生厌倦。况且幼吟的身籍仍在平安州,在京中不能盘桓逗留。待她离开,何愁不来!于是一时的门庭冷落并不以为意,不过付诸一笑,权当休息。
但直隶道花魁李名儿,却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物。眼见着京中相好上幼吟那儿去了不算,连自己在直隶道的恩客也长路迢迢赶去了清流坊。这便触了她的逆鳞。
某日雍王小宴,梁娉婷和李名儿陪侍左右。筵席之间,有个人喝多了些,恨道:“可恨那康与政,日日与我作对。又仗着家里颇有些资财,日日占着那花魁探花。那探花也着意于他。我送了多少黄白之物过去,偏不肯青目于我!”
李名儿心中一动,见雍王并几个上头人物已然走开,此刻只有几个闲散官员在场,便开言笑道:“不过是阿猫阿狗,玩意儿一般的东西,怎么这么眼皮子浅,看不上祝大人!须知祝鸿才祝大人乃是铁面御史,岂是她这等人能拣择得起的!不过,”
这话果然勾起了那人的好奇心,斜着眼问她:“不过什么?”
李名儿面上微微收紧,口中语言更加谨慎:“不过,我某次和她去陪侍,听她说,祝大人文才平平,却好讲道理,暗地里却不修私德。她实在,实在是厌烦得紧。所以并不想陪侍祝大人。”
祝大人勃然大怒,道:“某是何等人物,岂容她这个贱人如此信口雌黄!”
拂袖而去。
李名儿心中正在暗喜,一抬头,却见同样在座的梁娉婷用团扇掩面盈盈笑着,望向她的妙目之中,别有深意。
她心中一慌,转眼便又镇定下来。
果然过了不多时日,祝鸿才便上书当今,道是康与政贪污受贿,所得赃款甚巨。当今大怒,下令祝鸿才带头彻查。不想在康家和康与政老家,却并未搜出特别多的银两。
祝鸿才又奏道:“康与政家中没搜出赃款,必是将银两尽数搬与了与他相好的官妓。臣请将那官妓拿下,细细搜查为是。”
圣上准奏,于是幼吟的灾祸便来了。
【作者题外话】:希望有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