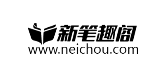福安沉重的脚步声消失在殿门外,承恩殿内死寂如墓。厚重的殿门隔绝了外界一切声响,只余烛火偶尔爆开的噼啪,和榻上那人微弱却总算平稳下来的呼吸声。空气里浓重的药味与血腥气,沉甸甸地压着,混合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带着死亡余韵的味道。
我僵立在角落的阴影里,后背紧贴着冰冷坚硬的殿柱,冷汗一层层地沁出,浸透了里衣,黏腻地贴在皮肤上,带来阵阵寒意。福安离去前那最后一眼的凝重,还有他指尖在太子颈下那一瞬间的、几乎无法察觉的停顿和瞳孔骤然收缩的惊骇……像冰冷的毒蛇,缠绕着心脏,越收越紧。
他看到了什么?
太子颈下……究竟藏着什么?
那秘密……是否与“青樾”,与“护城河”,与那道冰冷沉重的密诏有关?!
目光不受控制地投向榻上那张苍白脆弱的侧脸。烛光摇曳,在他挺直的鼻梁一侧投下深邃的阴影,下颌线条冷硬倔强。颈项修长,被月白色的寝衣领口半掩着,只露出上方一小段苍白的皮肤和清晰的喉结轮廓。
那被福安指尖触碰过的地方,就在右侧颈窝下方,靠近锁骨边缘……被衣领遮挡着,什么也看不见。
心悬在嗓子眼,每一次跳动都牵扯着紧绷的神经。巨大的好奇与更深的恐惧交织,如同冰火两重天。真相的碎片似乎就在眼前,却被一层薄薄的衣料和深不可测的迷雾阻隔。
福安的警告言犹在耳——殿下的命,就是你的命。
人偶的丝线,勒得更紧了。我深吸一口气,压下翻腾的心绪。现在不是探究的时候。至少,表面上,我必须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守夜宫女。
迈开因恐惧和久立而僵硬麻木的双腿,走到矮几旁。铜盆里的水还温热着。重新拿起一块干净的细白棉布,浸入水中,拧干。走回榻边,在脚踏上坐下。动作放得极轻,生怕再惊扰了榻上这具仿佛随时会碎裂的琉璃盏。
温热的布巾再次覆上他滚烫的额头。高热依旧未退,汗水源源不断地渗出。沿着他汗湿的鬓角,小心翼翼地擦拭。指尖隔着布巾,能感受到皮肤下异常的灼热和……一种细微的、因虚弱而无法抑制的轻颤。
布巾滑过他冰冷紧绷的下颌线。他的唇瓣干裂得更厉害了,几处裂口渗着细小的血珠,在苍白的底色上显得格外刺眼。取过另一块湿润的布巾,动作极轻地、一点一点地润湿那层死皮。每一次触碰都屏住呼吸,生怕他再有任何异动。
还好,他依旧深陷在昏迷的泥沼中,只有沉重而断续的呼吸显示着生命的顽强挣扎。
擦完唇角的血迹和水渍,布巾沿着他脖颈的线条,极其自然地向下擦拭汗湿的颈项。心跳,在胸腔里不受控制地加速。指尖隔着温热的湿布,触碰到他颈侧的皮肤,冰凉而细腻。
就是这里……福安指尖停顿的地方……
布巾的擦拭动作极其缓慢,极其轻柔。目光紧紧追随着布巾移动的轨迹,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
终于,布巾的边缘,极其小心地、带着一种刻意的“无意”,轻轻擦开了他右侧颈窝下方、靠近锁骨边缘的寝衣领口……
借着摇曳的昏黄烛光,那被衣领半掩的地方,终于暴露在视线之中!
不是狰狞的伤疤,也不是什么刺目的印记。
那是一块……玉!
一块半圆形的、温润莹白的玉玦!
玉玦不大,约莫拇指指甲盖大小,用一根极细的、近乎透明的天蚕丝线系着,紧贴着他颈下的皮肤。玉质细腻,在烛光下流淌着柔和的光泽。玉玦的边缘被打磨得极其圆润,触手生温。玉玦的正面,似乎……似乎雕刻着极其精细的纹路?
我的呼吸,在看清那玉玦的瞬间,骤然停止!
一股冰冷的、带着毁灭性力量的寒意,从脚底板瞬间窜遍四肢百骸,直冲天灵盖!浑身的血液似乎都在这一刹那凝固、冻结!
这玉玦……这玉玦……
不可能!绝不可能!
指尖因为极度的震惊和恐惧而剧烈地颤抖起来,几乎握不住那块湿漉漉的布巾!身体僵在原地,如同被无形的冰霜瞬间冻结!
怎么会在这里?!它怎么会在这里?!它应该在……
几乎是本能地、带着一种濒临崩溃的疯狂求证欲,我的左手猛地抬起,颤抖着、痉挛着,狠狠扯开了自己粗布宫女服的前襟领口!
动作粗暴,盘扣崩落!
粗糙的布料被扯开,露出同样苍白、却因激动和恐惧而微微起伏的颈项和一小片锁骨下方的肌肤!
就在左侧锁骨下方,靠近心口的位置!
那里,同样系着一根极细的、近乎透明的天蚕丝线!
而丝线的末端,赫然缀着一枚……与太子颈下一模一样的、温润莹白的半圆形玉玦!
烛光下,两枚玉玦隔着咫尺之遥,静静地躺在各自主人的心口之上,流淌着同样柔和、同样温润的光泽!
不!不是一模一样!
是……是一对!
这两枚玉玦,它们……它们原本就是一体!
它们能严丝合缝地……拼合在一起!
我颤抖着、近乎癫狂地,一把将自己颈下那枚玉玦扯了下来!冰凉的玉玦落入掌心,带着自己微弱的体温。目光死死地盯着太子颈下那枚玉玦的纹路,再猛地看向自己掌心的这枚……
玉玦的正面,精细地雕刻着半条……栩栩如生的鲤鱼!鱼鳞细密,鱼尾灵动,仿佛正在水中摆尾游弋!
而太子颈下那枚玉玦……那精细的纹路,是另外半条鲤鱼!鱼头昂扬,鱼鳍舒展!
当这两枚玉玦合在一起时,便是一条完整的、首尾相衔的阴阳双鱼!合则圆满,分则……永诀!
“阴阳鲤……不离不弃……”
母亲温柔带笑的声音,仿佛穿越了十年的血火与尘埃,清晰地响在耳边。
“樾儿,这玉玦,是你外祖家传下来的……娘亲一枚,你爹爹一枚……今日……娘亲把这枚给你……”
滚烫的泪水汹涌而出,瞬间模糊了视线!记忆的闸门被这冰冷的玉玦狠狠撞开!
十年前,护城河畔,沈府别院。
冲天的大火,凄厉的哭喊,刀剑的寒光,飞溅的鲜血……
混乱中,母亲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年幼的我死死压在身下。温热的、带着浓重铁锈味的液体浸透了我的衣衫……母亲染血的手,颤抖着,摸索着,将一枚带着她体温的、系着天蚕丝的玉玦,塞进了我的衣襟里,死死按在我心口的位置……
“……樾儿……活下去……拿着它……活下去……”
那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东西!是沈家……留给我的唯一念想!
这枚阴阳鲤玉玦的另一半,应该在父亲身上!应该在十年前,随着父亲的战死,随着沈家满门的覆灭,一起葬身于护城河边的火海与血泊之中!
它怎么会在这里?!
它怎么会……怎么会戴在太子萧彻的颈下?!
戴在……那个写下沈家满门抄斩令的刽子手的心口之上?!
巨大的荒谬感和灭顶的恐惧如同海啸,瞬间将我吞没!浑身冰冷,牙齿不受控制地咯咯作响。身体因为极致的混乱和冲击而剧烈地颤抖起来,几乎要从脚踏上栽倒下去!
是巧合?是仿造?还是……
一个更加可怕的、几乎将人彻底摧毁的念头,如同黑暗中探出的鬼爪,狠狠攫住了我的心脏——难道……难道当年护城河边,他……他也在场?!他不仅在场,还……还拿走了父亲身上的这半枚玉玦?!作为……作为屠戮的……战利品?!
这个念头带来的恶心和恨意,瞬间冲垮了之前所有因他呓语而产生的混乱和动摇!比密诏上的朱砂红字更刺目!更肮脏!更令人发指!
“呃……唔……”榻上的人似乎被我这边的剧烈动静惊扰,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眉头再次紧锁,身体不安地扭动了一下。
这声呻吟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瞬间冻结了我所有的失控和濒临崩溃的疯狂!
不能!不能被他发现!更不能被外面的人察觉!
我猛地攥紧掌心那枚冰冷的玉玦,尖锐的棱角深深硌进皮肉,带来尖锐的痛楚。用尽全身力气压下喉咙口翻涌的血腥气和几乎要破喉而出的尖叫!另一只手慌乱地、颤抖着将自己的衣襟拢好,遮住颈下同样的位置。
目光重新落回太子颈下那枚暴露在外的玉玦上。烛光下,那半条莹白的鲤鱼,仿佛在无声地嘲笑着我的愚蠢和天真。
恨意,前所未有的、带着血腥铁锈味的恨意,如同火山熔岩,在冰冷的心底轰然爆发!烧尽了所有迷茫,烧尽了那点可笑的动摇!是他!一定是他!是他亲手夺走了父亲的生命,夺走了这枚玉玦!是他将沈家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什么“该带你走”!什么“箭在弦上拉不住”!什么“天地同悲”!都是谎言!都是这个刽子手用来迷惑人心的鬼话!这枚戴在他心口的玉玦,就是最肮脏、最无耻的铁证!
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那道反复崩裂的伤口,鲜血顺着指缝渗出,滴落在冰冷的金砖地上,晕开一小点暗红。剧痛让混沌的脑子异常清醒。
沈青樾!记住这痛!记住这恨!记住这枚沾着父亲和沈家满门鲜血的玉玦!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毒酒……灌得好!他该死!他必须死!
就在这毁天灭地的恨意几乎要将理智彻底焚烧殆尽时,榻上的人再次发出更加清晰的、痛苦的呻吟。
“呃啊……疼……”他的声音沙哑破碎,带着浓重的鼻音,像是溺水的孩童在绝望挣扎。紧闭的眼皮下,眼珠再次疯狂转动起来,冷汗如浆涌出。
“冷……好冷……”他无意识地蜷缩起身体,双手紧紧抓住胸前的锦被,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身体筛糠般剧烈地颤抖起来,牙齿磕碰的声音清晰可闻。“……二哥……二哥……好冷……”
二哥?
这个陌生的称呼让我混乱的思绪再次凝滞了一瞬。他在叫谁?
然而,紧接着,更加混乱、更加痛苦的呓语如同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
“……别过去……青樾……别过去……有箭……有箭啊!!”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惊惧和绝望,身体猛地向上弓起,仿佛要挣脱无形的束缚!“……跑!快跑!别回头!!”嘶吼声在空旷的殿内回荡,带着撕裂般的痛苦。
青樾!又是青樾!而且……是在警告?!
“……弦……弦动了!拉不住!……父王!父王!不能放箭!不能啊!!”他像是陷入了最深的梦魇,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仿佛要抓住什么,又像是在徒劳地阻止着什么!“……血!全是血!护城河……红了……青樾……青樾别怕……二哥……二哥带你走……别怕……”
混乱的呓语如同无数根冰冷的针,狠狠刺入我的脑海!每一个字都带着血淋淋的画面感!
二哥?
青樾别怕?
二哥带你走?
父王不能放箭?!
父王?!先帝?!
难道……难道当年下令放箭的……是先帝?!而他……他当时在场?!他试图阻止?!他口中的“二哥”……是在叫他自己?!他……他想带我走?!
这个念头带来的冲击,比看到那枚玉玦更加猛烈!更加颠覆!
密诏上,是他亲笔写下的“诛灭九族”!
颈下,是他佩戴着本该属于父亲的玉玦!
呓语中,却是他绝望的警告和想要带我走的呼喊!
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
巨大的混乱和矛盾几乎要将我的灵魂撕成碎片!恨意在燃烧,那呓语中深切的悲恸和绝望却又像冰冷的潮水,试图将火焰浇灭。
“呃——!”一声撕心裂肺的痛苦嘶吼猛地打断了他的呓语!他身体绷直如弓,随即重重摔落!双手死死抓住胸前的衣襟,仿佛要将那颗跳动的心脏挖出来!那枚紧贴在他心口的玉玦,在剧烈的动作下,被扯得从衣领中完全滑出,莹白的光芒在昏暗的烛光下刺目地晃动着!
“噗!”一大口暗红色的鲜血,如同喷泉般从他口中狂涌而出!瞬间染红了明黄的锦被,也溅上了他苍白的脸颊和……那枚莹白的玉玦!
鲜血顺着玉玦光滑的表面蜿蜒流下,将那条半昂的鲤鱼染成了刺目的猩红!如同浴血的诅咒!
“殿下!”我失声惊呼,巨大的恐惧瞬间压倒了所有的混乱思绪!顾不上什么恨意什么玉玦,本能地扑上去!
他气息微弱,身体软了下去,再次陷入更深的昏迷。鲜血还在不断地从嘴角溢出,染红了半边脸颊和脖颈。那枚染血的玉玦,紧贴着他冰冷的皮肤,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来人!快来人!”我冲着殿门的方向嘶声大喊,声音因极度的恐惧而变调,“殿下吐血了!快传太医!”
殿门被猛地撞开!福安带着太医和几个宫人如同旋风般冲了进来!看到榻上那触目惊心的血污和奄奄一息的太子,所有人脸色煞白!
“快!施针!止血!”福安的声音都变了调,带着前所未有的惊惶!
太医连滚爬爬地扑到榻前,手忙脚乱地打开药箱。殿内瞬间乱成一团。宫女们端着水盆布巾,惊慌失措地围上前。
我被人群挤到了角落,背靠着冰冷的殿柱,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目光越过混乱的人群,死死地钉在榻上。
太医正在紧急施救,福安焦灼地在一旁指挥。宫人们手忙脚乱地擦拭着太子脸上和颈上的血污。
就在一个宫女拿着湿布,颤抖着擦拭太子颈下那片血污时,她的动作,极其轻微地顿了一下。她的目光,似乎在那枚染血的玉玦上停留了一瞬。
随即,她像是被烫到一般,飞快地移开了目光,更加用力地擦拭着周围的血迹,却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枚玉玦所在的位置。仿佛那是什么极其不祥的、不能触碰的禁忌之物!
福安就站在旁边,他那双精光内敛的眼睛,也极其短暂地扫过那枚染血的玉玦。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垂在身侧的手指,却几不可查地蜷缩了一下。
玉玦……
它果然是个秘密!
一个连东宫近侍都讳莫如深、甚至不敢触碰的秘密!
太医的银针再次落下,几处大穴被封住。汹涌的吐血似乎暂时止住了,但太子的气息却更加微弱,脸色灰败得如同金纸,仿佛随时会彻底熄灭。
“脉象……脉象极其凶险!元气大溃,心脉……心脉已如游丝!”太医的声音带着哭腔和绝望,“殿下……殿下这是……油尽灯枯之兆啊!除非……除非能有续命灵药吊住一口气,否则……否则……”
“混账!”福安厉声打断他,额角青筋暴起,眼神如同择人而噬的凶兽,“殿下若有不测,你们统统陪葬!给杂家想办法!必须把殿下救回来!”
“公公!公公息怒!”太医吓得魂飞魄散,扑通跪倒在地,“下官……下官定当竭尽全力!只是……只是殿下此番牵动的是陈年旧伤,心脉本就受损严重,此番又遭剧毒反噬和急火攻心……寻常药物……怕是……怕是难以回天啊!”
“难以回天?”福安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疯狂,“杂家不管什么寻常不寻常!殿下必须活着!听到没有?!必须活着!”他猛地转向身后一个心腹小太监,声音嘶哑急促,“去!把库里那支三百年的老山参取来!立刻!马上!”
“是!是!”小太监连滚爬爬地跑了出去。
福安胸膛剧烈起伏,目光重新落回榻上气若游丝的太子身上,那眼神里充满了焦灼、恐惧,还有一种……近乎孤注一掷的疯狂。他猛地转头,目光如电般射向角落里脸色惨白、摇摇欲坠的我。
“沈氏!”他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去!用参片!给殿下吊命!快!”
参片吊命?是指将参片含在舌下?
太医闻言,连忙从药箱里取出一个精致的乌木小盒,打开,里面是切得极薄、近乎透明的上好参片,散发着浓郁的药香。“沈姑娘,快!取一片,置于殿下舌下!”
我浑浑噩噩地走上前。看着太医捏起一片薄如蝉翼的参片。榻上的人,双目紧闭,唇瓣被鲜血染得暗红,干裂的缝隙里还残留着血沫。气息微弱得几乎感觉不到。
太医小心翼翼地将那片参片,试图放入太子微微开启的唇齿之间。
就在这时——
“咳咳……呕……”昏迷中的太子突然发出一阵剧烈的呛咳!身体猛地抽搐!那刚刚放入口中的参片,竟被他无意识的呛咳和呕吐反应,混着血沫一起喷了出来!落在染血的锦被上!
“殿下!”太医骇然失色!
“废物!”福安怒喝一声,一把推开太医!他眼中布满血丝,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疯狂,猛地看向我,“你来!用你的法子!必须让殿下含住参片!含不住,你就替殿下含着!用你的命,暖着它,渡给殿下!”
用我的命暖着它,渡给他?!
这命令,如同来自地狱的审判!冰冷而残酷!
我瞬间如坠冰窟!看着福安那疯狂的眼神,看着太医手中那片薄薄的、此刻却重逾千斤的参片……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快!”福安的厉喝如同鞭子抽在身上!
没有退路。人偶的丝线,勒断了所有的犹豫。
我颤抖着伸出手,从太医手中接过那片带着浓郁药香的参片。指尖冰凉,几乎感觉不到参片的存在。
走到榻边,俯下身。看着那张近在咫尺的、苍白染血的脸。浓重的血腥味混合着参片的异香,直冲鼻腔。恨意与巨大的恐惧在心底翻腾。
深吸一口气,带着一种近乎赴死的决绝。我伸出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那片参片。右手则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力道,用力捏住了太子的下颌,迫使他张开了嘴!
他的口腔里一片腥甜,舌苔厚重暗红。
就在我将参片送入他口中的刹那——
他那双紧闭的眼睛,竟猛地睁开了!
布满了蛛网般猩红血丝的瞳孔,带着极致的痛苦、混乱,还有一丝……茫然?涣散的目光,毫无焦距地、直直地撞进了我的眼底!
四目相对!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
他的目光,极其短暂地凝聚了一瞬,似乎认出了眼前这张脸!瞳孔深处,那混乱的痛苦中,掠过一丝极其复杂的、难以言喻的光芒——惊愕?困惑?还有……一丝……难以置信的……悲悯?!
随即,那凝聚的光瞬间涣散,被更汹涌的痛苦淹没。他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如同困兽般的呜咽。身体猛地一挣!被我捏住下颌的手,竟也猛地抬起,带着一种垂死挣扎的力道,死死抓住了我捏着参片、正欲送入他口中的左手手腕!
“呃……”剧痛从手腕传来!他抓的位置,正是之前被他攥出青紫指痕的地方!伤口被狠狠挤压,骨头仿佛都要碎裂!痛得我闷哼出声,几乎拿捏不住那片薄薄的参片!
混乱中,参片从我颤抖的指尖滑落!
而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
他那只抓住我手腕的手,不知是因为痛苦还是混乱,竟带着我的手腕,猛地向上、向内一带!
我的左手,连同那枚被我死死攥在手心、沾染了我掌心伤口鲜血的——那半枚属于我的阴阳鲤玉玦——被他那只垂死挣扎的手,带着一种巨大的、无法抗拒的力道,狠狠地……按在了他自己颈下那枚染血的、属于他的半枚玉玦之上!
“啪嗒。”
一声极其轻微、却在我耳中如同惊雷的脆响!
两枚染血的、温润莹白的半圆玉玦,带着各自主人的鲜血和体温,在混乱与剧痛之中,在濒死的挣扎之下,在福安和太医惊骇的目光注视中……
严丝合缝地……
拼合在了一起!
##第十章碎玉惊魂(下)
时间,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掐断。
空气凝固,烛火定格。
承恩殿内,只剩下两枚染血的玉玦,在太子萧彻苍白颈下,在沈青樾沾满鲜血的手掌下,拼合成一个完整的、首尾相衔的阴阳双鱼图。
莹白温润的玉质,被暗红的鲜血浸染,那条完整的鲤鱼仿佛在血泊中游弋,散发着妖异而惊心动魄的光泽。
“呃……”太子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的、意义不明的气音,抓住我手腕的力道骤然一松,手臂无力地垂落。那双刚刚睁开、布满猩红血丝的眸子,再次涣散,缓缓阖上。仿佛方才那瞬间的对视和挣扎,耗尽了他最后一丝气力。
而我,如同被施了定身咒,僵在榻边,左手依旧死死按在那枚拼合完整的玉玦之上。指尖能清晰地感受到玉玦光滑冰凉的触感,以及……玉玦下,他颈侧皮肤微弱却急促的搏动。
掌心伤口渗出的鲜血,和他颈上沾染的血迹,混在一起,浸透了系着玉玦的天蚕丝线,也模糊了玉玦的纹路。温热的、黏腻的触感,从指尖一直蔓延到心底,带来一阵阵剧烈的恶心和眩晕。
阴阳鲤……不离不弃……
父亲……母亲……
护城河……冲天大火……飞溅的鲜血……母亲塞进我衣襟的玉玦……父亲染血的战袍……
还有……颈下戴着父亲那半枚玉玦的……太子萧彻!
“二哥……带你走……”
“父王!不能放箭!”
混乱的碎片,带着血淋淋的画面,在脑中疯狂冲撞、旋转!几乎要将颅骨撑裂!
“沈氏!”福安那如同淬了冰碴的厉喝,如同惊雷炸响在死寂的殿内!
我猛地一个激灵,如同被毒蝎蛰到,触电般缩回了手!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踉跄一步,撞在冰冷的脚踏上,才勉强稳住。
掌心那半枚属于我的玉玦,已被染得血红,带着他的体温,死死硌在血肉模糊的伤口里,带来钻心的刺痛。而太子颈下,那枚拼合完整的阴阳鲤玉玦,依旧静静地贴着他苍白的皮肤,只是中间那道细微的拼合缝隙,已被两人的鲜血填满,仿佛从未分开。
福安几步冲到榻前,那双精光内敛的眼睛,此刻如同烧红的烙铁,死死地盯着太子颈下那枚完整染血的玉玦!他的瞳孔剧烈收缩,脸上惯常的刻板深沉被一种极致的震惊和……无法掩饰的恐惧所取代!那恐惧如此真切,甚至让他刻板的嘴角都微微抽搐了一下!
他猛地抬头,目光如同淬毒的利箭,瞬间钉在我的脸上!那眼神里,充满了惊疑、审视,还有一丝……难以置信的震骇!
“你……”福安的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压抑到极致的颤抖,他指着太子颈下的玉玦,又猛地指向我沾满鲜血、紧握成拳的左手,“你手里……是什么?!”
完了!
心沉入万丈冰窟!袖袋里有密诏,左手心是染血的玉玦,而太子颈下,是拼合完整的证据!
“奴婢……奴婢……”我张了张嘴,喉咙像是被滚烫的砂砾堵住,发不出任何完整的声音。巨大的恐惧攫住了咽喉,身体抖得如同秋风中的落叶。
“拿出来!”福安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不容置疑的杀意!他一步上前,枯瘦却带着千钧力道的手,如同鹰爪般,狠狠抓向我的左手手腕!
“公公!”太医惊恐的叫声打破了这致命的僵持,“殿下!殿下脉象快没了!”
这一声如同救命稻草!福安抓向我的手猛地顿在半空!他霍然转头,看向榻上气若游丝、脸色已呈灰败死气的太子,眼中那冰冷的杀意瞬间被更汹涌的焦灼和恐惧淹没!
“快!参片!!”福安厉声嘶吼,再也顾不上我,猛地扑到榻边,亲自捏起一片参片,试图撬开太子紧闭的牙关。
太医也慌忙上前,捏着银针的手抖得不成样子。
殿内再次陷入一片混乱的抢救之中。宫人们端着水盆、捧着药碗,如同没头的苍蝇。
我趁机飞快地将左手藏进袖中,用宽大的袖袍掩盖住那枚染血的玉玦和掌心的狼藉。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几乎要炸开。背靠着冰冷的殿柱,慢慢滑坐到脚踏上,将身体蜷缩进更深的阴影里。
目光死死盯着福安焦灼的背影,又扫过榻上生死一线的太子,最后落回自己藏进袖中的左手。掌心伤口被玉玦的棱角硌着,鲜血还在不断渗出,染红了袖口的内里。
玉玦拼合了。
父亲的那半枚,和他颈下的这半枚。
“二哥……”
那个在梦魇中绝望呼唤的称呼。
一个荒谬绝伦、却又带着致命吸引力的猜想,如同黑暗深渊中唯一的光亮,刺破了浓重的血雾——难道……难道太子萧彻……就是当年那个……护城河畔……母亲曾笑着提起过的……邻家二哥?!
那个总是翻墙过来,偷偷塞给她桂花糕、带她去看护城河边萤火虫的……沉默寡言的少年?!
那个在沈家别院大火前夜,还曾摸着她的头,笨拙地说“樾儿别怕,有二哥在”的……少年?!
不!不可能!
他是太子!他是萧彻!他是下令屠戮沈家满门的刽子手!密诏上的朱砂红字是他亲笔!他颈下戴着父亲的玉玦!这一定是掠夺!是亵渎!
可是……那声“二哥带你走”的悲恸呓语……那混乱中抓住我的手将玉玦拼合的举动……
混乱!前所未有的混乱!两种截然相反的认知在脑中激烈交战,如同两股狂暴的飓风,将我的理智彻底撕碎!
“呃……”榻上传来一声极其微弱的、如同叹息般的呻吟。
太医的银针似乎起了点作用,太子灰败的脸上泛起一丝极其微弱的生气,极其缓慢地、艰难地掀开了一条眼缝。
目光依旧是涣散的,毫无焦距地投向虚空。
“……樾……儿……”极其微弱、破碎的两个字,从他干裂渗血的唇瓣间逸出,轻得如同羽毛落地。
樾儿……
不是青樾。是樾儿。是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会唤的乳名!
福安的身体,在听到这两个字的瞬间,猛地僵直!如同被无形的闪电劈中!他捏着参片的手指,几不可查地颤抖了一下。他缓缓地、极其僵硬地转过头,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混杂着惊骇、了然和……更深沉恐惧的目光,死死地、死死地钉在了蜷缩在阴影里的我身上!
那目光,如同实质的冰锥,瞬间刺穿了我所有的伪装!
他知道!他全都知道了!从“青樾”到“樾儿”,从玉玦到身份!
人偶的戏,演到头了!
巨大的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将我淹没。完了。一切都完了。复仇尚未开始,身份已然暴露。等待我的,将是比死更可怕的结局。
就在这时——
“福公公!福公公!”殿外传来一个小太监带着哭腔的、极度惊恐的呼喊,伴随着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不好了!王将军……王将军带着人闯进来了!说……说有十万火急的军情!要……要面见殿下!我们……我们拦不住啊!”
王将军?北境戍边的王贲?!
殿内所有人脸色剧变!福安更是猛地站起身,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得干干净净!眼神中充满了极致的惊怒和……一种大厦将倾的恐慌!
“混账!殿下病重,岂能见……”福安的怒喝还未出口——
“砰!!!”
承恩殿那两扇沉重的殿门,竟被一股巨大的蛮力,从外面猛地撞开!
刺目的天光瞬间涌入昏暗的殿内!
一个身披玄甲、满脸风尘与煞气的高大身影,如同凶神恶煞般,大踏步闯了进来!沉重的战靴踏在光洁的金砖地上,发出沉闷而极具压迫感的回响!他身后,跟着几个同样甲胄染血、神色冷厉的亲兵!
浓重的血腥气和边关风沙的粗粝感,瞬间冲散了殿内沉滞的药味!
来人正是戍边大将,王贲!
他的目光如电,瞬间扫过殿内混乱的景象,扫过福安惊怒的脸,扫过太医惊恐的神情,最后,死死地钉在龙榻之上——那个面色灰败、气若游丝、胸前衣襟染满暗红血渍的太子萧彻身上!
王贲的瞳孔骤然收缩!脸上的风尘被一种极致的震惊和不敢置信所取代!随即,那震惊迅速转化为滔天的怒火和一种……深沉的、令人心悸的忧虑!
“殿下——!”王贲发出一声悲愤的低吼,猛地单膝跪地,声音如同受伤的雄狮,带着铁血的沉痛,“末将王贲!有十万火急军情禀报!北狄……北狄大军压境!连破三关!云州……云州告急!守将……守将战死!边关……危在旦夕啊!!!”
如同九天惊雷在承恩殿内轰然炸响!
云州告急!边关危殆!
而大胤的储君,帝国的定海神针,此刻却躺在龙榻之上,生死不知!
殿内一片死寂。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福安脸上的惊怒瞬间化为一片死灰。太医手中的银针“当啷”一声掉落在金砖地上。
所有人的目光,都带着绝望,投向了那个毫无声息的龙榻。
帝国……的天……塌了。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绝望死寂中——
蜷缩在阴影里的我,袖中紧握着那枚染血玉玦的手,指甲深深陷入掌心崩裂的伤口。
玉玦冰冷。
血,滚烫。
太子的生死,边关的烽火,福安的杀意,身份的暴露……所有的危机,在这一刻,轰然爆发!
【作者题外话】:爆肝到第十章啦决定分上下两块写,如果有人看就会写下去哒!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