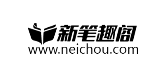叶吟风道:“世子莫非真要领兵驰援?这岂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
丁云桀却不认同,他望着叶吟风道:“不如虎穴焉得虎子?情势已然危急,不可再静观其变。”
叶吟风拢着眉宇,扬指欲斥丁云桀的鲁莽,碍于帝寅在身前而敛了敛心绪,他道:“君上,不知敌情者,不仁之至也,出征万里,需耗费民脂民膏,西周国库充裕也不得恣行,太后与文太师的眼睛正盯着您看!臣以为应当先派人察明实情再决议!”
丁云桀冷声道:“等察明实情盛慈就死了。”
叶吟风扭头望着他问道:“所以你便急着送命?”
帝寅忽道:“逸蒼,你以為淮永侯從何得知消息的?”
丁云桀思索一晌后道:“盛慈原是清麟军的校尉,与臣交情甚笃,当时臣受命戍守于平玉关力抗南晋,盛慈便是臣手下的副将,清麟军虽说大多兵权已挪交至臣的手中,军中不妨有些老将仍听从父亲调令,只是臣为避免盛慈为难,于是只将自己的亲信与新兵留在他手中,臣……臣想家父会比我还要早知道这消息,莫非是留在戍卫平玉关的清章军──”
“寡人已查明了,清章军有一小将名唤林桓,这林桓在你走后屡屡立下军功,短短期间内被盛慈提拔为了前锋,按理而言平玉关的军报每十天便会传回城中,而不知因何半个月前往来通信唯一路径的安夷犯了大水,致使军报晚了将近一个月。”帝寅目光定然落在丁云桀面上,有条不紊的与他说道。
而众人皆不吭声,帝寅接过了弥生掌中的折子,一面抛给了丁云桀,一面道:“所幸盛慈不愧是你手中出来的,往来传递军报的不仅只有明面派出一人,暗地里他安排了一个轻功一绝的将士,你们第一眼看见的军报是淮永侯派人截杀原传递军报的信使手中的,这一个才是平玉关真正的军报。”
班季生恍然大悟道:“淮永侯竟篡改了军报,若不是盛将军藏了一手──”他不敢说下去了,只觉得寒毛竖立,投向丁云桀的目光不禁只觉得他可怜,被亲生父亲算计手中的兵权还有命。
丁云桀因愠怒颈上冒出青筋,满怀痛恨咬牙道:“不单单只有如此,能使水灾严重至无法顺利通行,定是向来堤防丽川湍急大水的堤防被破了还可造成这局势,君上,安夷民情如何?”
弥生缓缓从地起身,他恭敬道:“回世子如今安夷死伤逾百,同有近七、八十人失踪,详情数目还需等前去指挥的沈大人来信方可知。”
帝寅望着面色青寒因愤怒忍不住颤抖的丁云桀,心中暗暗叹了口气,他将身子缓缓坐正,掌心搭在了膝上,金眸仅仅凝视着已然难以言语的丁云桀,寒声道:“逸苍,你要知道这几百条人命都是记在你的身上,虽说盛慈化解了危机,可他手中也死了近五十人,这一桩桩人命,都只是因你手中的兵权,若无盛慈的谨慎,兴许你的命也栽进去了。”
“你总是不愿寡人出手你与淮永侯的事,从前寡人是同意的,毕竟寡人只是个外人,可如今淮永侯已经出手伤及西周子民与戍卫西周的将士,此时寡人不会再袖手旁观。”
丁云桀眼皮都没有抬,果而向帝寅道:“臣谨遵吾王圣命。”
帝寅转眼望着叶吟风道:“寡人已经让振雪调回城中,并任清麟营指挥使,原职的空缺你找个人补进去,还有这折子是寡人对多年金戈铁马的淮永侯的慰问,三人大人若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今日便退下罢。”
.……
西周平朔三年,五月。
周王以淮永侯数十载为西周疾驰沙场立下汗马功劳,后文又道丁云桀乃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虽道玉不琢不成器,而今丁云桀已然琢玉成器为栋梁之材,丁氏满门赤胆忠烈,震古烁今,国士无双,封淮永侯为郡公,另赐金银、彩缎、马匹等,並御赐牌额。
这消息传到宣齐郡公府时,阮知梦正挽着母亲的手在园中消食谈天,元宁长公主倒是不以为然,母女二人走到亭中坐下稍歇。
阮知梦有些诧然道:“这不是明摆着叫丁伯父致仕交权么?”她扭头望着硃砂,“是何牌额?”
硃砂垂首回道:“回县主君上御笔亲赐‘勤慎元辅’四字。”
元宁长公主忍俊不禁地笑了声:“君上这四字正是送给淮永侯……不,如今要称公爷了。”她的眼底尽是鄙夷与几分的欢喜,心中替盛夫人这些年的际遇感到舒心不少。
阮知梦道:“可丁伯父真就会心甘情愿的交权么?”
元年长公主不置可否道:“妳认为丁仲岐手中还有什么权?雖不知丁仲岐被君上抓了什麼把柄,可顯然這是君上念在丁仲岐這些年來為西周立下的功勞給他台階下,妳以為武將都是痴愚的?錯了。”
阮知梦知道母亲虽只是一名女子,少时却有睥睨须眉的本事,并与盛夫人是闺中挚友,无话不谈,盛夫人嫁给淮永郡公时元宁长公主甚为盛夫人添了不少嫁妆,之后虽各嫁为人妇可交情依旧,当元宁长公主听说夏姨娘一事气得就拿剑要冲去当时的侯府。
眉眼疾色,毫不遮掩,每当元宁长公主想到盛夫人红肿的双眼,恨不得剜下丁仲岐与夏姨娘身上的肉,甚至好几回都想将盛夫人接走,纵知不符礼节,可她如何能冷眼看着盛夫人受苦,万幸的是丁云桀有出息。
元宁长公主望着阮知梦道:“囡囡,妳也挑些贺礼给郡公府送去,我就想给丁公爷锦上添朵花。”
阮知梦忍不住抽了抽嘴角,忍着笑向母亲点头。
……
望舒坐在马车上,一改平日的鹤氅,穿上了檀色襦衫梳着双丫髻,与司锦与阮知梦坐在了马车上,望舒有些不习惯这衣着,亦时不时想伸手摸一摸头发,僵立着背脊万念俱灰的坐着,引得在旁的二人不迭的笑意。
从前她亦想穿上鲜丽曼妙的衣裳,可当如今真正穿上方知多么不自在,一日两日尚且可忍,但她是要穿这样进宫中见周王的,不禁心中感到一阵难为情。
车内阵阵喧哗嬉闹在快到了淮永郡公府门前便停了,掀起车帘能看见御赐四字‘勤慎元辅’,不知道丁仲岐看在眼中何等刺痛?他虽已过盛年尚能驰聘沙场,却被周王逐出朝堂中心,封赠的荣衔是周王给了彼此一个台阶下,丁仲岐心有不甘亦不可驳了周王的面子,只得拜表辞官。
马车渐渐停下,司锦先行下车后望舒随即下车,一人一边扶着阮知梦下马车,望舒与司锦齐步在阮知梦身后缓步走入淮永郡公府,阮知梦从小便常到淮永郡公府玩耍,故此下人们都知道这位贵人,阮知梦向来只带硃砂或嘉月,突来一张新面孔不禁引人侧目。
远远地三人便见到丁云葵下了学堂向着这方向走来,阮知梦迅而回首向二人示意眼神,阮知梦在丁云葵走近时先向望舒低声一句“对不住”后张手掴了望舒一个耳光。
“哪来的毛丫头这般不知好歹,若不是硃砂与嘉月今天有事忙,我也不会带妳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东西出门,一出门就给我丢人现眼的。”
望舒扑通一声便跪在地上向阮知梦磕头,听闻喧哗的丁云葵踩着小碎步跑了过来,她张着嘴纳闷地望着跪在地上的望舒,挽住了阮知梦的手问道:“梦姊姊,这是谁啊?妳家的丫头?”
阮知梦点头道:“硃砂前些日子从牙婆手中买来的,妳也知道嘉月要嫁人了,一开始瞧着她手脚伶俐原以为是什么勤快聪明的丫头,没想到痴愚又爱偷懒,说什么都不听、不做,敢情我才是她的丫头,她是我的主子。”
丁云葵皱眉道:“哪有这种事,不省心的东西再让硃砂找人牙子给卖了。”
阮知梦轻嗤了声,望着丁云葵挤眉弄眼道:“那也得你哥哥同意。”
丁云葵一怔又问道:“怎么又与我哥哥有关系?”
阮知梦道:“你哥哥那个好色的登徒子,前些日子来我那喝茶,居然说要我把这丫头送给他!”
丁云葵气得直跺脚:“那怎么行?我哥哥快与苏家姊姊成亲了,怎容这种小狐狸在旁边!司锦!赶紧叫人牙子来,把她给我卖了!”
司锦无奈道:“可世子千叮嘱着奴婢不可以让人动了她……”
丁云葵一下便睁大了眼睛,跑到望舒的身前大声喊道:“妳!给我抬头!”望舒闻言抬起了脸,颤颤地望着丁云葵,丁云葵瞧着她哼了一声,“都没有司锦好看,我哥哥是蝙蝠看太阳瞎了眼?妳就喊人牙子来,出什么事我给妳担着!免得又生出什么事端,耽误了哥哥和苏家姊姊喜事。”
阮知梦连忙出手拉了拉丁云葵:“小葵、小葵,妳听姊姊说,妳哥哥一直念叨着丫头不是寻常丫头,还不许我随便卖了!我今日就是找她来问妳哥哥究竟葫芦里卖什么药。”
“远远就听见妳再说我坏话。”丁云桀从另一条小径走了过来,司锦与他示意一眼后,司锦便走到了丁云桀的身后,丁云桀伸手将望舒从地上拉起,“我说妳俩是嫌我不够乱?还处处给我添乱?”
丁云葵挣脱了阮知梦的手,冲到丁云桀面前没好气怒道:“哥!给你脸皮你不要脸,还是糨糊洗脸脑子不清了?你都要娶苏家姊姊入门了,居然还看上这种小狐狸,苏家姊姊知道得有多伤心?今日无论你怎么说,我就是要找牙婆把她给卖了,最好卖出城!”
丁云桀伸手拉着丁云葵的耳朵,丁云葵吃疼的跺脚喊着:“妳个丫头,家里事如今由妳做主了?知梦糊涂妳也跟着胡闹?我是瞧这丫头丹青不错,要送她入宫给君上的,”话落,他又狠狠地拽了一下,丁云葵捂着耳朵跑到阮知梦身后,“君上喜欢画鹰啊燕的,偏偏这丫头将那大鹰画的威风,你们两个都是名门贵女,整日学着那些村妇七嘴八舌,成何体统?”
阮知梦狠狠地瞪了丁云桀一眼,演戏归演戏,没料到她居然说她是长舌妇:“你早说便是,我没想到硃砂去牙婆那挑的丫头还有这独一门的本事,不過,這丫頭是我買的,你要把她從我手上送給君上,好歹也给跟我买罢。”
丁云桀撇了撇嘴,不敢置信地望着阮知梦,戏却不能不演下去:“司锦,把钱给县主,然后把这丫头带下去,明日带她进宫给君上瞧瞧。”一面说着,一面暗骂着阮知梦。
而阮知梦从司锦那收了钱,啧啧地向着望舒笑道:“这可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妳明日就好好画个大鹰给君上,也省得在我府中做那些杂役。”
“是,谢谢县主。”望舒尴尬笑道。
丁云桀望着司锦吩咐道:“带她下去罢。”
“是。”
司锦向望舒示意一眼后,望舒便跟着司锦一同离去。
丁云葵见状向着二人道:“哥哥、姊姊,我先回房了!妳俩好好聊!”话落,脚步如有风般一下便溜走了。
丁云桀哭笑不得地望着她狼狈逃跑的背影,一晌,扭首向阮知梦道:“去我屋中喝杯茶?”
“世子请。”
“县主请。”
……
屋中清谧,屋外皆是他的影卫,于此亦不怕丁仲岐的眼线,方才那一齣戏是演给丁仲岐看的。
阮知梦捧着手中的茶碗,看着丁云桀道:“我并不知道丁伯父落了什么把柄在你与小乙手上,但是他定不会善罢甘休,何况我一直以为他背后应当有人,是太后还是文太师?又或者是旁人。”
丁云桀牵着一抹微笑:“妳不觉得很可笑么?我与他身上流着世上最亲密的血脉,却为了手中的兵权步步算计、步步为营,他恨啊,他恨他为西周荣辱一世,却因一次的错误而被夺去手中的兵权,西周的半壁河山诚然有他的一份,若我是他,我定也不会善罢甘休。”
“若那次不是你與盛慈以命為注,如今湖州便落到東齊手中,先王與小乙待他已是仁至義盡,‘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先王待他不好?小乙待他不善?若淪為旁人早便誅九族了,”她瞟了瞟丁雲桀陰鬱的面色,無奈地歎了口氣,“逸蒼,你們父子反目早在三年前便落下了引線,你視他為父,可他卻將你當作阻礙前程的擋路石。”
见丁云桀迟迟不语,阮知梦起身寒声道:“你再这样慈悲心怀,迟早有天害死盛伯母与小葵,届时你追悔莫及。”话落,挥袂迈步便离去,茶碗中的茶都没有喝上一口。
在旁接替司锦伺候的司命抬首望着丁云桀道:“主人。”
丁云桀忽地笑了数声,他步步缓慢地走了出去,走在廊上咏颂道:“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言毕,复是一声长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