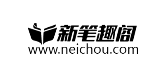等一堆人处理好伤口后,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消毒水的刺鼻和劫后余生的疲惫。篝火的余烬噼啪作响,映照着几张沾满硝烟与泥土的脸,疲惫而警惕。就在这短暂的、虚假的平静中,黑瞎子动了。
他像一道无声的阴影,脚步踩在潮湿的落叶上几乎没有声音,但那股冰冷的杀意却如实质般弥漫开来。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原本松弛的神经瞬间绷紧。他径直走向那个缩在树根阴影里的伙计——就是之前背刺任雨生的那个伙计。伙计脸上充满了心虚,恐惧。
冰冷的金属触感抵上叛徒的额头,他惊恐地抬起头,“别…黑爷…”叛徒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嘴唇惨白,“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鬼迷心窍了!饶…饶我一次…”他涕泪横下,身体筛糠般抖动,死亡的恐惧瞬间压垮了他。就在刚刚,他还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任雨生细致包扎的服务,仿佛那场致命的背叛从未发生。
任雨生的心猛地一沉。他看着黑瞎子稳如磐石的手臂,看着那支抵在叛徒眉心的枪,枪管在篝火余光的映照下闪着无情的幽光。就在几分钟前,他的手指还按压在这个人肮脏的伤口上,清理、止血、包扎,那是他作为医生刻入骨髓的本能。此刻,那处包扎好的伤口在叛徒剧烈的颤抖下,似乎又有血丝渗出,染红了纱布的一角,显得格外刺眼和讽刺。
“饶你?”黑瞎子的声音低沉得如同深渊里刮过的风,每一个字都带着千钧的重量,敲打在每个人的心脏上,“饶你,兄弟等着再次在背后下黑手吗”?
他的手指稳稳地搭在扳机上,那细微的动作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周围的伙计们屏住呼吸,没人敢出声求情,也没人敢表示赞同。因为他们也怕自己在前面奋斗的时候后背被人背刺,丛林里只剩下叛徒粗重绝望的喘息和篝火余烬的噼啪声。
“瞎子!”任雨生猛地站起,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急迫,“等等!”
黑瞎子的动作顿住了,头微微偏向任雨生,墨镜反射着跳跃的火光,看不清情绪,但那股锁定猎物的气势并未转移:“雨生?你要替这杂碎说话?”他的语气里没有疑问,只有一种冰冷的、审视的意味。仿佛在问:你刚流的血,这么快就忘了疼?
任雨生深吸一口气,压下肋下伤口传来的隐痛和心中翻腾的复杂情绪——对背叛的愤怒,对生命的本能维护,以及对黑瞎子此刻决绝杀意的理解,甚至是一丝恐惧。他直视着那副墨镜,试图穿透镜片看到黑瞎子的眼睛:“不是替他说话。他该死,这点我比你更清楚。”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冷静与决心。
“不必脏了自己的手,把他留在这里”。任雨生向前一步,目光扫过周围紧张沉默的众人,“我们刚死里逃生,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伤,筋疲力尽,该保存好体力。”
他顿了顿,目光再次锁定黑瞎子:“清理门户,我赞成。但得挑时候,挑地方。至少,让我们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喘口气。到时候,你想怎么处置,我绝无二话。但现在开枪,浪费不必要的精力”。
黑瞎子沉默着。枪口依旧死死顶在叛徒的额头上,那叛徒已经被吓得几乎失禁,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怪响。时间仿佛凝固了,只有丛林的湿气包裹着他们。黑瞎子淡定自若的收了手,就好像刚刚想动手的不是他一样。
“好,听你的,雨生。就让他多喘几口气。”他微微俯身,凑到叛徒耳边,声音如同毒蛇吐信,“听见了?你的命现在留下来了,现在的路该你自己走了”。
说完,黑瞎子闪电般地用枪柄狠狠砸在叛徒的后颈上。叛徒连哼都没哼一声,像一滩烂泥般瘫软在地,昏死过去。
“捆结实,嘴堵上。”黑瞎子直起身,声音恢复了惯常的冷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走吧,雨生说得对,此地不宜久留,马上动身。”他扫了一眼任雨生,那眼神复杂难明。
众人都明白这道上行走的人最恨的就是背叛,刚刚在青年的劝说下,黑爷已经手下留情了,但那人也不可能在这种场景下活得下去,即使侥幸活下去了也不会再有人敢用他了。
危机暂时解除,但空气并未轻松。任雨生看着地上昏迷的叛徒,又看看黑瞎子挺拔却带着浓重杀伐之气的背影,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接下来的路一定并不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