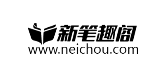麟德殿的喧嚣与赞誉,如同退潮的海水,一夜之间便消散无踪。取而代之弥漫在大兴城上空,尤其是晋王府周围的,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氛。
晋王杨广将自己关在书房内,往日里挺拔的身姿此刻显得有些佝偻。
父皇在朝会上那雷霆般的震怒,依旧在他耳边轰鸣。
那些刻薄的言辞,诸如“浮躁冒进”、“不恤民力”、“有损圣德”,像一根根冰冷的针,刺穿了他骄傲的外壳。
更让他心寒的是,太子杨勇站在班列之中,虽未直接落井下石,但那微微上扬的嘴角和眼神中一闪而过的轻松,却比任何攻击都更让他难受。
“本王一心为国,何错之有?!”
杨广猛地将案几上一只精美的越窑青瓷茶盏扫落在地,碎裂声在寂静的书房里格外刺耳。
他不过是想尽快将小舅舅独孤信带来的祥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力,证明自己的才干与效率,为何会引来如此多的攻讦?
“殿下,息怒。”
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如同幽潭之水。
许国公宇文述不知何时已悄然立于房中。
他挥手让战战兢兢的侍从退下,亲自掩上了房门。
“事已至此,愤怒于事无补。”
“息怒?叫本王如何息怒!”
杨广猛地转身,眼中布满了血丝,“王诚、李俭那几个太子的鹰犬,咬住此事不放!还有伍建章那老匹夫,也跟着推波助澜!他们这是要将本王彻底打落尘埃!”
宇文述的神色依旧平静,仿佛外界滔天巨浪与他无关。
“殿下,您错在两点。其一,操之过急。‘萃盐法’虽利大,然牵扯甚广,民力、农时、地方官府协调,千头万绪,岂是一道王府谕令便能速成?其二,越权行事。此等涉及国计民生之大事,当由陛下下旨,户部统筹,地方执行。您以亲王之尊直接插手,且方式激进,便是授人以柄。”
杨广张了张嘴,想要反驳,却发现宇文述所言句句戳中要害。
他确实是太心急了,被那巨大的盐利和潜在的功绩冲昏了头脑。
“那……如今该如何是好?父皇命我闭门思过,盐务交由太子……这岂不是将到手的功劳拱手让人?”
他语气中充满了不甘。
宇文述微微摇头道:“殿下,此刻已非功劳之争,而是圣心之争。陛下震怒,非因盐法本身,而是因您行事之方式,触碰了他最看重的‘稳’字与‘民’字。当务之急,是设法平息陛下与皇后娘娘的怒火,挽回圣心。至于其他,需从长计议。”
杨广颓然坐回椅上,双手捂面。
他深知宇文述说的是对的,但挽回圣心,谈何容易?母后那边……他几乎可以想象到母亲那失望的眼神。
与此同时,皇宫凤仪殿内,独孤伽罗也确实正为此事忧心忡忡。
她屏退了左右,只留下贴身的年老宫人,对着窗外的宫墙默默出神。
“娘娘,喝口参茶定定神吧。”老宫人轻声劝道。
独孤皇后接过茶盏,却无心饮用,叹了口气:“本宫这几个儿子……勇儿性子软绵,缺乏主见;广儿倒是有魄力,却这般急躁冒进,如此心性,叫本宫这为娘的如何放心?”
“晋王殿下或许只是年轻气盛,想为陛下和娘娘分忧……”老宫人小心翼翼地为杨广开脱。
“分忧?”
独孤皇后放下茶盏,语气带着一丝愠怒,“他这是添乱!陛下与本宫辛苦经营,方有今日局面,最忌的便是这等扰民之举。他倒好,一纸命令下去,惹得地方怨声载道!这岂是人君之道?”
她最气的,或许不是杨广犯错,而是他犯错的方式,触及了她与杨坚共同的执政底线。作为母亲,她心疼儿子受责;但作为与皇帝并称“二圣”的皇后,她更无法容忍这种可能动摇国本的行为。
就在这满城风雨,晋王府门庭冷落之际,一个身影却晃悠到了宫门口——国舅爷独孤修。
他这几日过得颇为惬意。
皇帝的赏赐堆满了库房,走到哪里都能收获或真或假的恭维。然而,他今天也听说了杨广被训斥的消息,心中不免有些嘀咕。
倒不是多么深厚的感情,而是出于一种“我看好的人怎么这么快就要凉了”的简单想法,以及一丝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因“萃盐法”而起的内疚。
“我得进宫去探个究竟。”
他吩咐家丁备车来到皇宫。
……
“阿姐!”
他像往常一样,笑嘻嘻地闯入凤仪殿,却敏锐地察觉到殿内气氛不同往日,姐姐眉宇间笼罩着一层化不开的愁绪。
“阿九来了。”
独孤皇后勉强笑了笑,招手让他近前。
“阿姐,您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告诉我,我帮您出气!”
独孤修凑上前,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
看着他这副天真不知愁的样子,独孤皇后心中的烦闷稍减,又是叹了口气,将杨广之事简单说了一遍,末了痛心道:“阿摩(杨广小字)这孩子,往日看着稳重,怎此番如此不知轻重!真是让本宫失望透顶。”
独孤修听完,眨巴着他那双清澈的桃花眼,脸上先是茫然,继而露出恍然大悟,还带着点自责的神情。
他拽着独孤皇后的衣袖,用力摇了摇,用带着委屈的腔调说道:
“阿姐!原来是因为这个!您错怪阿摩了!要我说,这……这都怪我!”
皇后一愣,被他这没头没脑的话弄糊涂了:“怪你?此事与你何干?”
“对啊!就怪我!”
独孤修用力点头,表情无比“真诚”。
“阿姐,您想啊,我那‘萃盐法’,在宫宴上是不是显得特别简单?好像随便找口锅,弄点粗盐、木炭、棉布,三下两下就搞定了?跟变戏法似的?”
独孤皇后回想那日情景,点了点头:“确实神奇,过程也看似不难。”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主角一拍大腿,脸上写满了“懊恼”。
“阿摩他肯定是看我做得那么容易,轻松愉快就把事情办成了,就觉得这事儿一点都不难,这才想着要快点干成,好为您和姐夫分忧,让朝廷早点用上钱!他这是一片孝心,也是想为国出力啊!他哪里能想到,这‘看起来简单’的事,真要推广到全国,会有征发民夫、耽误农时、协调官府、计算钱粮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麻烦事?这就像……就像我看厨子炒菜,觉得翻几下锅就好了,真自己上手,连火都生不起来!”
他顿了顿,总结道,语气更加“沉痛”:
“他这是被我那‘简单’的演示给误导了!以为这是件能立竿见影的容易事,所以才犯了急性的错误!这说到底,是怪我考虑不周,没提前跟他说清楚这背后的艰难!阿姐,您要罚就罚我吧!别生阿摩的气了,他也是一片好心办了坏事!”
这一番话,如同孩童呓语,却又逻辑自洽,合情合理。将一个复杂的政治错误,巧妙地归结于一场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技术性误会”。
独孤皇后听着这番“孩子气”却又角度清奇的分析,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
是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都能当场做出来的东西,谁会觉得它背后关联着如此复杂的民生政务呢?阿摩定然是求成心切,被那“简单”的表象迷惑了,本质还是好的,是为了孝顺父母、报效国家。他的错误,在于年轻,在于不懂具体政务的复杂,而非品行或动机有问题。
想到此,她心中的失望和怒气,瞬间被一种“孩子还小,需要慢慢教”的无奈和宽容所取代。
她伸手轻轻点了点独孤修的额头,语气已然缓和:“你呀!就会胡搅蛮缠!罢了罢了,此事阿姐心中有数了。你也少往晋王府跑,安心在府里读书,莫再惹出事端。”
独孤修乖巧地应下,心中却暗松一口气。
他知道,姐姐这关,算是过去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他这番看似“甩锅”的辩解,很快便通过皇后的心腹,传到了禁足的杨广耳中。
晋王府。
原本深陷颓丧的杨广一听到内宫传来的消息,第一时间猛地从坐榻上站了起来。
他先是愕然,随即是难以置信!
最后,一种混杂着巨大感激、庆幸与一丝莫名酸楚的情绪,如同汹涌的潮水,瞬间冲垮了他这些日子以来用愤怒和骄傲筑起的堤坝。
在他众叛亲离、被父皇严厉训斥、被朝臣落井下石、甚至连母后都对他深感失望的时候,竟然是他这个平日里只觉得有趣、并未真正放在平等位置上看待的小舅舅,用这样一种看似幼稚荒唐、实则精妙无比的方式,为他化解了最关键的母后那边的压力!
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政绩,没有攻击政敌一句不是,只是轻飘飘地将一切归咎于“演示太简单造成的误导”。
这简直……简直是神来之笔!
这需要何等的急智?
又需要何等……赤诚的回护之心?
杨广在书房内来回踱步,心潮澎湃。
他发现自己以前完全低估了这位小舅舅。
独孤修拥有的,不仅仅是那些奇思妙想的“格物”之术,更有一颗七窍玲珑心,以及在这冰冷宫廷中极为罕见的义气!
“备车!不……不必声张,准备一顶不起眼的小轿。”
杨广压下激动的情绪,对心腹吩咐道,“待禁令解除,本王要亲自……不,是秘密请小舅舅过府一叙!”